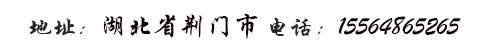散文你我终究是来客
|
夜已深,寂静和孤独包围着我。暂居城中村斗室的窗子外面,不时响起过往汽车的汽笛声,不时传入我的耳朵里,这声音好像提示着我:还有人在这个城市忙碌着。 此时的我已经躺在了床上,开了一晚上车的我此刻睡意全无,心里想的全时房贷,装修贷,微粒贷和支付宝等各种还款项目啥时候能还上盘算着自己微薄的收入能否把这些“窟窿”填满。真是愁煞人啊! 我住的城中村听说今年12月底就要拆了,真是几多欢喜几多愁,我可能是属于后面“几多愁”里的一分子吧!唉,拆了再搬家吧,反正搬家又不是第一次了!来西安打工我都不记得自己搬了多少次家了,总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自己连一块地方也没有。 谁让我是来西安的打工者呢?谁让我是最底层的劳动者呢?谁让我是租不起单元房的穷小子呢? 以上三句话绝不是什么抱怨和矫情,这是我真实的处境,这种处境我很焦虑也很厌恶,但作为打工者你只能接受,接受这不“公平”的境遇。谁让我是这座城市的“来客”呢?! “来客”,一个形容从外地来到谋地工作的“异乡人”。来客是一个境地尴尬情感更尴尬的一部分人。 境地尴尬:不是这里的人,你得从语言和处事方式跟本地人学。情感尴尬:人在异乡心系故乡。这就是来客,这就是来客所有的尴尬所在。 故乡是多么柔多么软,多么可爱多么美丽的地方啊,至少是在游子和来客的心里是这样的,其实故乡对于所有人都这样的。故乡是每一个人情感的血地,这里有他稚嫩的童年,这里有他青涩的青少年,这里最主要有他的至亲父母和父老乡亲…… 贾平凹说过:“故乡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父母不在了,故乡就成为了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地名。”父母在我们情感有依托,父母不在了我们就成了情感的“弃儿”。父母是我们维系故乡情感的唯一纽带,没有父母在的叫家,有父母在的叫——故乡。 故乡,一个多么温暖的名词啊!对于来客来说,故乡时常是梦里的地方、心里的地方,往往不是拼搏的地方,拼搏的地方在——城市。为了城里格子楼上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我们背上了行囊远离、淡漠了故乡;为了能融入城市,我们学着城里人说话,走路,进酒吧,喝咖啡,为了能出人头地,我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不那么像农村人,其实我们骨子里还是农村人。 我们住在城市一住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我们对于城里道路和街道的熟悉程度比对故乡还熟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想融入城市就得拼命熟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待在城里的时间绝对比待在老家的时间长久。回老家,除非家里或者亲戚朋友有事你才回去,回去待不了几天你就返回城里。你和故乡的接触都是匆匆忙忙回,匆匆忙忙走,总是匆匆忙忙的…… 我们淡漠了故乡,淡漠了乡邻,有的多年不回老家的人,见了村里人未必能按辈分叫正确称谓;与其说我们忙在城市,不如说我们亏欠了故乡。对于城市我们是来客,可对于故乡,我们更像是“来客”…… 我不知道是该可怜还是该憎恨?可怜的连个根都没有,憎恨的我们都失去了“故乡”,这或许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吧! 我们就像是穿梭于南北往来于春秋的鸿雁一样,衔着故土的春泥,翻千山越万水,经风雨战严寒,一路奔波一路歌地飞来飞去,总是飞不停,说到底只是一个劳燕分飞的来客而已。 故乡——城市——来客,两个地方一个人,人就像一个梭子一样——穿来穿去,他到底是属于城市呢还是农村?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 小时候看母亲在织布机上织布,把一个两头尖的梭子从左手穿到右手,穿来穿去觉得挺好玩。如今年齿大了,体悟到自己何尝不是那个织布用的梭子呢?从左手扔到右手,你说它是右手的还是左手的?两个手都抓住过它,两个手都没抓住它,它只是织布用的,只有织布时它来穿来穿去的。 如果说生活是一台织布机,左手是城市,右手是故乡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是那个穿来穿去的梭子,至少目前是,目下的时代是。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gtoujiana.com/dtjzz/11528.html
- 上一篇文章: 青璇的宠文已是不错,可天下归元女帝本色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