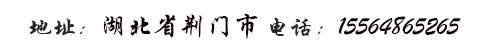父亲的四次战ldquo疫rdquo
|
钱启同,原温州二医(医院)内科名医,年以百岁高龄辞世。此文为其长女所作。——编者 父亲钱启同13岁考上浙江省立十中(今温州中学),受陈叔平先生的影响,对数学很有兴趣,且成绩优秀,深得陈叔平先生的赏识,理想在数学上有所成就。18岁陪童年好友去杭州参加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考试,没想到被录取,父亲没想去读,可他的奶奶很满意。因为父亲幼年父母双亡,爷爷也因病早逝,家中因病离世的人很多,奶奶最担心这个宝贝孙子,最怕他也被病魔缠上,如今他糊里糊涂考上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奶奶觉得这是天意,一定要父亲去。父亲最听奶奶的话,就这样,他放弃了数学的理想,改学医科。既然学了医,父亲就想和他大姐夫一样去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深造。他从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后,为了省钱,想先在国内学好日本语,再去日本。由大姐夫缪澂中介绍,进入济南日医院学习,但当年(年)就因济南五三惨案真相逐步揭露,当他得知中国人遭受日本人杀害的真相后,医院,也放弃了留日深造的决定。之后,他先后在山东枣庄、浙江杭州和江苏盐城等地工作和学习过,积累了一定的临床医学经验。年,钱启同在杭州浙江医专细菌学自费实习时与家人合影,左一为本文作者。年,江西京赣铁路恶性疟疾半年时间里,父亲累瘦了,还没有拿回来一分钱工资年,江西恶性疟疾流行,在京赣铁路施工的北方工人,因没有对疟疾的抵抗力,大批人相继死亡,很多工人也应恐疟逃亡,直接影响了京赣铁路的施工,父亲就是这时被紧急调往京赣铁路,在离贵溪30里地的洪峦村东医院。当父亲赶到时发现,这里已经有50来个病人,可父亲领到的装备只有二百粒奎宁丸、几针奎宁针和三十包硫酸镁,天平、量杯都没有,却要面对50来个急等救助的病人。连抱怨的时间都没有,父亲先给几个高烧的病人打了退烧针,医院。医院就“建在”东岳庙,周围搭起工棚,这就是病房,戏台下面做门诊室,戏台上是医生的“宿舍”。医院就这样算是建立起来了,由父亲负责,当听到局方弄到百两装的罗氏奎宁粉十箱,配给他们,已运到洪峦镇,父亲担心战时混乱,怕这些奎宁粉丢失,连夜冒着风雨,在泥泞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赶到洪峦镇,第二天就冒冒失失雇了几个保定的工人,让他们把药运往东岳庙,自己先赶回东岳庙为病人治病,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紧!大家都问他怎么不跟着抬药的工人,他说,自己在北方多年,觉得北方人很讲义气。好在,第二天药品还是完好无损地送到了,大家都笑他“呆人不怕鬼”。药是拿到了,可只有奎宁,书上说,恶性疟奎宁是治不了的,一定要用扑疟母星阿的平治,难道就看着那么多患恶性疟疾的工人死去吗?父亲不信,难道缺医少药的时候就不看病吗?父亲亲自给重症病人灌肠、换药,当时生活条件很差,病人脏得如同叫花子,清洗非常麻烦,父亲从不嫌弃,担任医生兼清洁工,亲力亲为深得工人爱戴,甚至连精神病人都听他的话。父亲主张预防为主,叫每个工人定期吃奎宁粉预防,药苦,工人不肯吃,他自己亲自吃给他们看,工人备受感动,都主动吃药。父亲又规定重症病人住院,医院给药、给伙食,轻病门诊,医院只给药,这样既减轻了病人的负担,医院的压力。为了改善重症病人的伙食,医院的经费不够,父亲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天气转凉,工人都没有棉被和衣服,父亲又拿出自己的工资买煤,生火取暖,为防止火灾,三更半夜还亲自起来巡查。而父亲自己吃不好睡不好,还整天与恶性疟疾打交道,可他自己始终没有被传染,大家都说他是善有善报。在父亲等人的精心治疗和对病患的体贴关怀下,只靠奎宁药,恶性疟疾不到半年就得到了控制。在江西治疗疟疾的半年时间里,父亲累瘦了,还没有拿回来一分钱工资,他说:“这点钱能救活那么多病人,我很欣慰,你们也不是没饭吃,苦一点能锻炼意志。”年,瑞安鲍田地区霍乱当姑妈做好饭,端来时,发现父亲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抗战爆发后,日本“细菌部队”对浙江多地实施了细菌攻击,使得多地烈性传染病爆发。年4月间,父亲的好友张景飞奉命创建浙江省第八区中心卫生院,地址选在墨池坊十六号(房屋现在依旧存在),父亲应邀协办,他关掉自己的诊所就去了。医院建好没几天,当年夏,霍乱大流行,尤其是瑞安鲍田地区,一天都能死十几个人,父亲与张景飞的共同好友钟铎,准备在鲍田南河塘设临时霍乱收容所,集中治疗,张景飞大力支持,派父亲和护士金月眉、李叔湘三人去协助。那时药品器材很缺,只买了化学精制食盐和化学精制苏打。没有蒸馏器,就用烧烧酒的烧壶代替。没有输液针筒,就用旧的两头尖空盐水瓶代替。他们用棉花纺绸做滤纸,垫在漏斗上过滤;在旁边水井里汲水,自烧蒸馏水,自制生理盐水,消毒后给病人输液。第一天就收了40来个病人,之后不断地来,十个针筒连续不断地注射,父亲他们四个人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因为输液及时,制剂新鲜,无致热原质,注射后毫无发热反应,救活了许多人,且收到隔离的效果。他们半个月就煞住疫势,共收容了87人,只死了7个人,简直是医学奇迹。有意思的是,当时除了钟铎全家四人,不为名利,全部加入服务外,其余帮忙者均为地方上毫无医学知识的无业游民。因为当时流传霍乱流行是阴间拉壮丁,农民连街上都不敢走,谁敢来接近病人。只有这些游民,无家无室,才敢来帮忙,得到重用的游民还很负责。由于父亲他们的防疫措施做得好,没有一位帮忙者染病,也算是奇迹。以后父亲常举这例,告诫我们:“说明天下本无不可用之人,只看你用得是否得当。”当疫情得到控制后,有一天父亲抽空去前池看他二姐。二姐看到小弟弟,高兴得不得了,她知道弟弟在鲍田抢救病人,还听说成绩不错,知道小弟一定累坏了,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吃饭了没有?”父亲对姐姐倒是没有客气,直接说:“饿死了。”姑妈立即去做饭,她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做给弟弟吃。当姑妈做好饭,端来时,发现父亲坐在马桶上睡着了,姑妈心痛得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她想叫父亲去床上睡,又怕一叫醒父亲他马上又要走。举棋不定的姑妈在马桶前来回转悠,终于发现父亲醒了,姑妈立即跑去热饭,顾不得讲究了,端上一大碗泡饭,站在刚离开马桶的父亲面前,急急忙忙说:“赶快吃,吃完再走!”父亲就这样,狼吞虎咽吃完了姐姐端上的美味佳肴,抹抹嘴:“我走了!”父亲就是这样在亲友的娇宠下,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治病救人中去。年,温州城区鼠疫她问母亲:“你信什么佛?”母亲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信钱启同!”刚平定了鲍田地区的霍乱,父亲回到了八区中心卫生院,没想到鼠疫又来了。龙泉是鼠疫疫源地,年自龙泉运来一批茭白,里面发现一只死鼠,只因不知这是只鼠疫疫鼠,还是把货物存放在西郊镇宁巷一家堆栈,结果引起鼠类鼠疫大流行,很快蚤类就带上了鼠疫病毒。年,西郊街上随时发现爬不动的疫鼠,人类也出现了腺鼠疫死亡病例。因发现疫区在西郊,于是把八区中心卫生院改为温州传染病院,迁到西郊油车巷的大庙,父亲他们都成为防疫人员,穿上防蚤衣,去灭鼠看病。省卫生厅还派来一个外国人伯力士,办鼠疫训练班。起初发现都是腺鼠疫,局部淋巴腺肿痛厉害,体温达40度以上。当时用口服消治龙、肌肉注射鼠疫血清来治疗,晚期病人死亡率还是很高。就在大家忙碌时,不知为什么,省卫生厅搞人事变更,派赵竟初来当院长,赵还带了自己的一套人马,父亲他们也就只好辞职,回家开诊所。谁知很多医师很怕鼠疫传染,就把病人推到私人诊所,因为我家诊所早就配备了显微镜,诊断的准确率高,介绍到我家的病人特别多,真是门庭若市。父亲天天出诊看鼠疫,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全家也都穿上防蚤衣,帮助父亲接待病人。因为公家不出诊,父亲与柯主光平分了全城鼠疫病人的出诊,父亲负责西片区域。父亲决定不卖药,药品由病家向药房自购,我们代为免费注射,深受病家欢迎。当时打锣桥一条街都是棉花店,疫鼠发高热寒颤,钻进棉花里,人们取棉花,就被已感染的疫蚤叮咬,由此被传染。父亲走遍了信河街72巷,有时出诊,遇见病人,才发现是鼠疫,防蚤衣也没带,可父亲没有半句推辞的话语,马上诊治。我们很抱怨,说他不顾及自己的安全,也不顾及家人的安全,父亲回答说:“不是我不怕死,既然做了医生,不去救病人,良心说得过去吗?”父亲的敬业让我们无话可说,特别是我们的母亲,对父亲的敬业极为赞赏。多年后的一天,母亲遇见去进香回来的表妹的婆婆,她问母亲:“你信什么佛?”母亲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信钱启同!”父亲竭尽全力医治鼠疫病人,被他医治的病人不计其数,其间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有关鼠疫的知识。可当时还是战时,完全隔离做不到,加之运输线被阻断,医药跟不上来,完全控制鼠疫还是很难做到,直到温州第三次沦陷,全城疏散,鼠疫才消失了。年,温州城区霍乱父亲掷地有声地答道:“我就是要跟阎王抢人!”年夏,全市霍乱又大流行,父亲和张景飞医院,因为没有政府拨款,也没有类似基金会的组织在经费上支持,只得借用清明桥外崇仁社的18间殡舍。这是一个寄放棺木的地方,那几年瘟疫猖獗,抬棺材的师傅生意特好,民间都说那是霉头年,阎王抓壮丁来了,我忧心忡忡,对父亲说:“你们选个好点的地方嘛,医院呢?”父亲掷地有声地答道:“我就是要跟阎王抢人!”说完,头也不回直奔清明桥。医院由父亲负责,他与戴守侠、林荣澄等制定总的医疗方案,同时请来许多临时医师,因为有前期鲍田的经验,他们安排医师日夜三班轮流抢救,因抢救及时,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无一死亡,成绩为温州历来霍乱救治之冠。这年父亲一个夏天都没有洗过澡,考虑到病人的卫生环境,他总是匆匆赶回家,换身衣服又上战场,妈妈也只能是心痛地站在门口,目送他渐渐消失的背影,然后进屋立即清洗消毒父亲换下的衣服,晾干,叠好,等他来换。据说,当时抬棺材的师傅一下子没有了生意,好纳闷,到处问:“哪里请来的神仙?”回答是:“钱启同!”父亲由此名声大振。我的父亲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就这几次临时负责,打的都是漂亮仗,不能不叫人佩服,叫人难忘。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gtoujiana.com/dtjzy/8740.html
- 上一篇文章: 假期攻略回家不吃这些东西,一定会后悔
- 下一篇文章: 蜂房不光止痛,还抗癌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