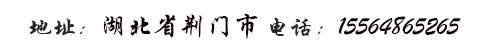小白后金宝
|
白癜风能治疗好么 http://pf.39.net/bdfyy/bdflx/190522/7157873.html 后金宝 □小白 后金宝是个村子。这么说就应该有一个前金宝,一般一个行政村都有几个自然屯,一社、二社、三社……东五、西五什么什么的。这里有后,当然就得有前吧。可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却从不知道前金宝在哪。去我们这个村五七百米,正南是一片庄稼地,东南是一个民用飞机场,西南边也是块地,庄稼地前边是一条国道,直奔黑龙江,国道南边倒是有很大一片人家,可那已经是城郊了,该不会那里有个前金宝?后金宝离城也不远,去年又重修了道,更是好走,从我家开车,一脚油门,十几分钟,到了。 本来这个农村小院我是打算给我二姐一家住的,那时候她的孙子小,儿媳妇在外地支教,孩子撒不开手,没来上。我跟她描绘这处蓝图时,她听得眼睛呆直,斜看着天棚,计算着养多少只鸡鸭,喂一头肥猪,冬天支上个大棚种菜……后来好歹孩子大了些,媳妇也调回了城里,她却害了一场大病,撒手走了。这里于是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一来,我就难过。 这两年我一个大哥领着他老妈在这种种园子,换常住上几天,春天下地栽秧、备陇,夏秋拔草、除虫,倒也满园绿色,瓜菜常鲜,一家人其乐融融,这个院子也就好歹算是适得其所了吧,终于没有荒废。今年老太太身体不如以前,没有了种地的心劲儿,一帮儿女自然也就散了,本来就是哄老人开心来的。好在一伙朋友不嫌麻烦,兴致勃勃的接管了过去,刚一进清明就开始策划,今天拉粪,后天旋地,忙得不亦乐乎,几个人经常为这个种的不对,那块苗栽密了,起了争执。现在一看,园子给他们侍弄得比之从前还更像那么回事了。 村子小,不到二百户人家,青壮年都携妻带子的外出务工去了,走不了和不愿意走的就只剩下六七十个老弱病残,每天撑着炊烟照常升起。村里偶尔传来一声公鸡打鸣,几声狗叫,反倒衬得这里更加寂静了。村子里房屋盖得参差错落,不甚规则,整体呈两头尖,中间粗的形状,地势东高西低,远看就像个织布梭子,静静地躺在粗经大纬的麻布上。 进村只有一条官道,打西边来,从一个液化气站下道,冬天,枝叶萧条,大地捂在白茫茫的雪里,屋瓦上也零星积着没化的雪,沿着树趟子走不远就看见麻哒哒的村落。夏天,夹道两边的树木就变得愈加粗大繁茂,天上的枝杈交叉纠缠在一起,棚起一道浓荫。大地里,苞米密密扎扎的铺天盖地,满世界的绿,那就只有走出浓荫,房屋才在绿里冒出个头。在这喧闹的城市才几步路,就得到这么一处桃花源般的村庄,也算不多见了。 这里每家的院子都极宽绰,似乎当初盖房子,只要你顾得上,就能可劲的圈地。也或许是一家人走了大半,儿子、姑娘几户人家并成了一个大院子,留给老人看管着,所以就显得更大了吧。 进村有一排破旧的砖房,看来已荒废多年,院子更大,不知道是谁干什么,在这个院子里取土,挖了很大很深的一个坑,坑里堆满了垃圾,垃圾上长着一人来高的蒿草。从规模上看,它最早应该是一个村办企业,房子的门窗都破了,穿过黑魆魆的洞口,能看见里边是车间或者库房一样的格局,不是住人家的样式。大门两边的砖墙上用水泥砌着五角星,院墙多数已经坍塌,只有靠房根儿的一截仍然沧桑地挺立着,和五角星一起坚持着从前的记忆。 村里不常见着外人,三两个老太太抱着孙子在道边靠着院墙唠嗑,刚会跑的大点的孩子就在道上耍,乍乍吧吧的一会儿追鸡,一会儿撵狗,扑通卡一个跟头,哭两声,见没人嘞,抹一把鼻涕,爬起来接着跑。有车进村,就都停下手里的活计,一把扯过孩子,相跟着追看去了谁家。你若问路,老头会放下园子的活儿,连喊带比划的说的极仔细,见你仍没言语,会跳出院墙一直把你送到村头,左上坡,右下道的指引着方向,那副急迫的眉眼,生气了一样,仿佛他已经看到了你要去的目的地,咧着嘴,一下子逮住了你的笨拙和愚蠢了。 居家的大爷大妈城里大多也都有房子,他们不愿意去住,嫌那里憋屈。一家一个鸟笼子,悬在半空,住半个月,对门姓什么都不知道。上广场瞅人家老头老太太跳舞、耍扇面、打太极拳,这咱哪会呀?!想搭咕句话,人直躲,一脸的嫌弃。再不去遭那个罪了,实在是数九寒天,嘎嘎冷得不行,上楼猫两天冬,烘烘暖气就得了。还得是农村自个家大院子,喘口气都痛快,天都比城里的高,星星都比街里的大。一铺大炕烧透透的,烙得人翻身打滚,得劲,咯的骨头节都开了,腰板烫溜直。一口大锅什么炖不得,电饭锅做的饭怎么能跟大锅捞的米比呀,那才叫香。 我就想起了我的老父亲,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老了那天跟我一起上楼,可惜我不争气,到他走,也没混上个楼,始终也没能满足他老人家跟老儿子享福的心愿,哪怕只有几天呢!他也到我城里的小院来过一趟,那时候城里还有不少平房,家里算院四五十平,住不下,只呆了一天,他上我家跟前的商场给孙女买了一个带轱辘能牵着走的塑料小花狗,反复叮嘱我要交到闺女手上,我下班的时候他还在厨房忙,一块抹布投了又投,水舍不得倒,大马勺底儿给他擦的锃亮。这又勾起了我对水的记忆。 小时候我们家的园子也是非常大的,每到春夏的傍晚,我的痛苦就来了,天天一放学就浇地,一放学就浇地,那时候感觉家里好像有浇不完的地。院子里那口洋井似乎是我的专利,我被父亲催逼着,无处可逃的拴在上面不停地压呀、压呀、压呀……水就被父亲一桶又一桶的拎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儿,累得趴在了井把子上打了瞌睡,忽然一个激灵醒过来,却发现父亲已经很久不再送桶过来了,听见他和母亲在月亮底下的园子里说话,浑身竟一下子精神起来,心里又升起了说不出的高兴。 现在村子里已经有了自来水,也是去年挖的。电闸一合,水哗哗的就流了出来,地可劲儿的灌,在没有了记忆里的辛苦,可也再不会有父亲的声音了。原来,我压出的井水里是有着那么多甜蜜的时光的,它的涓涓细流流淌的竟然是岁月赐予我们一家人的香甜。一时间,我把这水流当成了亲情接力的火炬,就是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手机信号一样,接通过去和现在的时光,我只想告诉老父亲,思念其实并不难过,难过的是他们一走,就彻底的把我们忘记了。 不知道村子里那些在外打工的兄弟姐妹们生活过的都怎么样,现在的农业生产跟从前是不一样了,家家那晌八亩地用不着那么多人忙活,赶上农忙,抽空回来几天就把地种下了,大田几乎不用铲什么地,现在这农药真厉害,比人都认得苗,能让你光长苗不长草!秋下回来雇个收割机,两天就完事了。由此看来,这些出去的人还都是些勤快人。 在早年间,山东人闯关东为了活命,后来江浙人进关里是为了生计,在近百年里,东北人的传统一直都是老守田园,轻易不远行的,“半晌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我们延续的生活信条,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没什么事,出去干什么呢!现在看来时代是真变了,文化也变了呀!南人不在北顾,北人却纷纷远赴关外。 这里的大多数村子,天天静悄悄的,都难得听见几声燕子的呢喃,南方的生活有那么好吗,竟连它们也不再愿意迁徙?还是地里的虫子也给农药都药绝了? 前几天我在小院里干活,忽然听见几声燕子的呢喃,忙抬头四处寻找,两只小天使在房山上的电线上叽喳,可不真是它们吗!你们是从我的少年飞来的吗?不知不觉间泪水竟然流了一脸。我们的家乡不好吗!不好吗?这里有父母在,一庭一院都在,从小尿过的土炕还热着,灶台的炉火没熄,地里的苞米藏得住人。家家接着自来水,户户亮着电灯泡,村村连着公路,怎么就比不上外边呢?!陶渊明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都荒了,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再怎么说家里还有老父守望“稚子候门”。古意和现代文明是冲突着的吗?如果可以,我愿意活在古意里。 快到端午了,端午过后,后金宝的小园儿黄瓜就能做纽儿了,过两天打开天,麻椒得间间苗,确实栽密了。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小白,本名赵东海,国网吉林白城公司工人,喜读书,偶有感触发于笔端。 我心我书 请扫上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gtoujiana.com/dtjyl/10916.html
- 上一篇文章: 面的一千种吃法,搓鱼不是鱼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