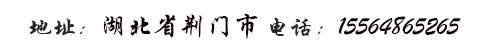超低调的免签小岛活火山,原始社会,成龙
|
耶稣火山之夜,原始菜市场,学插花的孩子 ——享乐瓦努阿图之一 如果我没有喝过瓦努阿图当地的土椰子,一定不会想到,卖菜的土著会拿芹菜给我当吸管。 踏上瓦努阿图Tanna岛耶稣火山的路途是颠簸的,伴着火山轰鸣,越野皮卡车在黑沙的火山路中艰难行走。 陪伴我的除了司机Jack,还有一位美女是当地的原住民,司机的妻子Nancy,黝黑而粗糙的皮肤,卷卷的头发,一身淡黄色连衣裙下,怀着6个月的宝宝,因为他们家住在火山脚下,所以就顺路搭我们的车。 皮卡摩擦地面沙沙作响,进行得非常慢,Jack说:“现在的路已经好多了,可以将车开到山脚下,去年都只能开到火山进口处,也就是我家附近,再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山脚。” “这只能证明路修得更长了,但是路的质量没有变化吧?”我笑着问。 Tanna岛就这一条路,做生意的小贩和学校等公共建筑就在两旁,一路上都能听见Jack和外面打招呼, 大家互相认识,此地没有陌生人。 路边的时不时出现的一些用原生态木条搭建的棚子,只有少数的有顶,上面堆放着什么看不太清,只看到路边有些当地特有的绿色大香蕉。 Nancy对我说:“这些是我们的菜市场,那些木架子上放的都是蔬菜水果,后面那些……”她指着那些挤在一起坐在地上的妇女们,“就是卖菜的。” “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对于菜市场的文化,我总是很好奇。 它代表了当地的生活,无论是沙迦菜市场热火朝天的拍卖和井然有序的规划,还是加拿大温哥华格兰维尔岛的被鲜花和艺术包裹的市场,或是印度瓦拉纳西的人与牛食物与牛粪共融的魔幻世界……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和信仰,在菜市场中呈现的冲击和对比最明显。 在Tanna岛,我触摸到原始的菜市场。 从车上下来,就发现每个人的眼睛都盯在我身上,应该很少黄皮肤光临他们的商铺吧。 我扫了下四周,这才发现那些坐在地上的妇女,不是手中抱着孩子的,就是挺着肚子和Nancy一样有生孕的。 看他们被晒的黝黑而粗糙的皮肤,从脸到身体到处的皱纹,怎么看都像是近半百的人,却因为这些孩子让我想到,也许她们才不过二三十岁。 走到每个摊子,或品尝或挑选,都没人管你,直到你要称重付款时,才有妇女懒懒地从地上起身来到你身边。 Nancy说她们卖的菜也都不是他们种的,谁想免费吃都可以自己去采摘。 “那为何她们卖还有人买呢?” “因为她们挑选了最好的,有的食品,像这个……”说着她拿了一个烤黑了的玉米,“还经过了她们的烹饪,所以她们卖的主要是劳动力。” 她们就是原始社会中的海淘卖家吧。 Nancy拿过了一串食物递给我:“你猜这是什么?” 竹签上串了七八个食物,长得像白蘑菇,但用手捏它又发现很硬。 将它从竹签上取下,会发现它整体的形状像是扇贝,上下两部分紧紧咬合在一起。 “你尝尝?”Nancy鼓励我试试味道。 “可以直接吃?”我掰了小块放嘴里,有些许甜味,入口后粉粉的:“是菱角的味道!” 当我像Nancy描述菱角时,显然她没有见过这种两头尖尖身体黑的食物,她告诉了我这个像扇贝的菱角的名字:Namambe。 那忙贝(音译)。果然,还是贝类的一种,笑。 我问Nancy:“你们这里的香蕉比我吃过的都大,不知道好不好吃?” “我们没有直接吃过,但听Jack的老板说不能直接吃。” “那你们怎么吃呢?” “打成泥,做成香蕉饼。” 几家摊子一下子就看完了,结束时,发现Nancy买了一大堆菜。 我惊讶地望着她:“你买了这么多菜?是要储存起来过冬吗?”她没有笑,倒是在思考,看来我这句冷笑话她没听懂,这么一个热带地区哪里有冬的概念嘛。 就听她认证地告诉我:“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这句令我瞪大了双眼,光她抱着的那一大捧南瓜藤,大到可以把她整个人藏起来。 “你家有几口人?一顿饭吃这么多?” “我、Jack、四个孩子、爸爸妈妈、三个哥哥、嫂子、他们的孩子……”她板着手指算得仔仔细细,是个大家庭。 我不可思议地问:“你家有几口人你不知道吗?” “嗯……这个……没算过……”尴尬的笑容第一次出现在她脸上。 紧接着第二次尴尬的笑容出现,是她送了我一个土椰子。 卖椰子的妇女用刀在长了毛的椰子上钻了个口,递给我。 “怎么喝?”我疑惑。 “对着嘴喝。”卖椰子的妇女说。 仰起头,我将嘴对准椰子口,都90度直角了,一滴椰汁也没流出来。 妇女用刀将洞戳大一些,有椰汁流出了,但我觉得凭我嘴再用力吸,也就只能喝到不足一口的量,于是放弃。 Nancy要妇女给我找根管子,就见妇女到摊子上找了根芹菜,将根取下,塞进椰子口:“诺,给你,这样就能吸出来了。” 望着眼前这根比我嘴都宽的芹菜根,我转头看看Nancy,她尴尬地笑着点点头,示意我可以试试。 果然,椰子水出来了,但喝像太不雅观,惹得那一群坐在地上的妇女们都哈哈大笑起来,Nancy也憋不住噗嗤笑出后,前仰后合。 我抱着椰子走到那帮妇女中间,坐下,将椰子递给她们,让她们试试,她们赶紧摇头,把手放在嘴上做羞愧装。 我看没人喝,我就又吸了一口,她们紧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可以穿破天际,爽朗开怀不顾形象的。 我想,艺术家高更接触大溪地妇女时,看到的是一样的景象吧。 他把她们留在画板上,我把她们留在镜头中。 砰!一声闷响! 随着Jack将皮卡启动离开市场,火山发出了第一声欢迎。 开了不多一会儿,Nancy要我等下,她去学校接一下孩子,一起回家。 所谓的学校。就是马路边的两间平房。 平房外,站了有一百多孩子,穿着统一的浅蓝色衬衫,黑得发亮看不见五官的脸,短而卷的头发。 我问Nancy:“你认得出哪个是你的孩子吗?” Nancy再次露出尴尬的笑容:“我认不认得出他没关系,他认得我就行。” 白眼啊,这么心大的妈妈,莫不是开玩笑吧。 事实证明,她真的没开玩笑,到我们要离开时,她孩子也没来找她,她就要Jack晚上再来接一次,就真的离开了。 “你就这么走了?!”我惊叹,完全不可置信。 她继续尴尬的笑容,点点头:“晚上Jack送你回酒店时,再来接他,老师会照顾他的。” “那他不吃晚餐啦?” “我们会等Jack和他回家后再吃的。” 还真是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生活。 在她去寻找孩子的短暂时间,我也下了车,跟她一起走进孩子们中间。 和卖菜的妇女一样,这些孩子也很少有机会能见到我这样面孔的新鲜人,都对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但与那些妇女不同的事,这些孩子很主动地凑到我身边,我大声喊:“Hello!”他们就跟着兴奋地回应:“Hello!” 一时间,我被这一百来号孩子们包围了,裹得我里三圈外三圈。 我问Nancy她孩子叫什么,Nancy告诉我后,我冲孩子堆里喊:“Peter!” 没想到大部分男孩子都举手,不知道是他们都叫这个名字,还是逗我玩。反正Nancy没有因为孩子躲起来紧张,反而对我眨眼:“也许他现在还不想回家。” Nancy用手指了指挤在我身边的孩子拿着的花:“这些花是要送给这个外国哥哥吗?” 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手上大部分都拿着花花草草,应该是从路边摘下来的野花野草。 没想到小朋友听到Nancy这样问,羞着脸把花立刻放到背后,完全没有给我的意思。 当我的眼睛扫到其他拿花的小朋友,也一样反应。 这可让我好奇心大增,他们要拿这些野花做什么呢? 校长兼今日唯一值班老师,是个个子很高很壮挺着大肚子的中年男子,他给我们解惑。 “今天我们学习插花课,这些孩子手中的花草,是他们的作业,所以不能给你呢。” 插花课?我没听错吧! 这个词组好像和日本家庭主妇的闲暇时光有关,又或者与一些商业课程有关,居然会在这么一个随时可以钻木取火的小岛上出现? 尤其是学习这堂课的还是一群不过小学一二年级的原住民小朋友! 让我汗颜,好像在我们的教育中,美学并不是重点。如果要学插花,也许就是为了开花店,学艺术,就是为了办画展…… 而这些孩子,他们的学习并没有太多的目的性,也并不为了让他们当一个插花师或开花店,就是仅仅的感受美。 在匆匆忙忙的当下,每分每秒都在变化莫测的世界,已经留给我们很少时间去感受美的存在了。 在火山山脊处,Nancy要和我告别了,她和一帮像是高中才放学的瓦努阿图男孩一起,往大山的深处走去。 火山再一次喷发,比上次的声音大了许多,我终于走到它的脚下。 就见Nancy一排人逐渐走远,在一圈又一圈、像是水流形状的干燥地貌中,他们走了很远很远,但依然能清晰得看得见他们的身型、服饰、动作。 就像是一幅会活动的油画,因为一望无边的风景,全部尽收在眼底,视野非常开阔的同时,也可以很清晰地描绘出所有的细节。 此时此刻,就只有我,和皮卡车,一阵风吹过,将宇宙的喧嚣都带走了。 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 除了火山黑沙摩擦鞋底的沙沙声,荒芜的空气中,写满了寂静。 厚厚的白云沉沉地压在连绵的山顶,深呼一口气,都能听见心跳的震动,和火山、和整个世界融在了一起。 闭上眼,我,即是全世界。 美女蕾蕾在进山口等着我的到来。 蕾蕾是当地今年仅有不多的豪华酒店EverGreen常青酒店的女老板,也是我这次在Tanna岛入住的酒店。 在她和她先生的精心打造下,酒店呈现了多种风貌:中式的园林、罗马式的建筑、东南亚式的房间、希腊式的泳池…… 还有被南太平洋包围的风景,穿着脚蹼下水便能与珊瑚热带鱼浮潜,可谓瓦努阿图的迪士尼。 因为她是唯一住在岛上的华人女性,所以在瓦努阿图这个小国家非常出名,好像谁都认识她似的,在维拉港时就有许多人推荐我入住她的酒店。 当我问她:“是什么原因让你留在了瓦努阿图?” 她哈哈大笑地,水塘里的鱼听到都赶紧游开:“因为这里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简单的四个字,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次数已太多。 云南洱海的Ana开了一家有猫陪伴的咖啡厅,清迈的辣辣和先生共筑了名为童话的乐园,加德满都的Amber为了爱情成为了摄影师的妻子兼搭档…… 她们都是琼瑶笔下爱做梦的女孩,为了梦可以不管不顾放下一切去追梦。但她们又不似琼瑶笔下的女孩那般柔弱,而是像金庸笔下的江湖女子,用结实的灵魂和披襟斩棘的态度,将梦想抓在了手中。 在做梦这件事上,女人比男人更知道如何追求幸福。 鸭舌帽,粉红镶金字的运动短袖,牛仔短裤,非常具有活力的一个女生,白皮肤的她,与黑皮肤的那一群正在祭祀山神的原住民相比,形成极大的反差。 游客不能擅自登山,需要在登山口与同时间登山的其他国度的陌生人们,组成一个个登山小组,由当地人引路,再搭车乘坐半个小时左右的颠簸山路,方可到山脚。 出发前,又一个短暂的祭山神仪式。由居住在山里的某个村落来进行。 像是村长的人孤独地坐在一角,沉思冥想,并没有电影中出现的那种跪拜或烧火场景。 当我们这些他乡来客在互相认识,热闹畅聊时,村长凝视着脚下的土地,时不时捧起黑沙放在手心,再任由它们从指缝中流走。 时间在当地人的眼中,是不是也和沙一样,捧起,或流走。 据说在村长沉思祈祷的过程中,如果火山喷发,就不允许上火山。 当地人说是火山有选择游客的权利,我觉得是出于安全。 不过很奇怪的是,明明喷发很频繁的火山,此时倒真的很安静。 当村长站起身后,仪式正式开始,村子中的一群男女穿着草做的裙子走进了众人的视线。 男的光上身,女的上身也披了件草衣服,头上插着两根羽毛,问其这羽毛代表了什么,她们回我:“为了表演需要。”还真是个实在人。 当他们给每个人献了花,拉着我们手拉手跳了段舞后,每个分组便坐上了敞篷的拖车部分,进山! 蕾蕾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中充满笑意:“如果不是你要我陪你来,我都好久没来了。” 我也跟着笑。因为我们俩的缘分差点就失之交臂。 来Tanna的飞机每天一班,商务10点准时起飞的小飞机。 来之前的一天,我在维拉港定的车,问司机几点到机场合适,司机拍着胸口说:“9:00从你酒店出发就行。” 从酒店到机场开车20分钟,踩着9:20我来到机场,值机的人员告诉我已经关闭登机口了。而那些已经有登机牌的人,排队开始登机了。 我和蕾蕾“天啊,宝贝,我去不了了!” 电话那头的她也是紧张万分,全然想不到会出现这种乌龙。在我漫长的旅行经历中,这也是第一次误机,之后也发生了一些有趣而光怪陆离的故事,等下篇文章与大家讲述。 蕾蕾成了那一天我联系最多的人,我在干什么吃什么玩什么,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给她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gtoujiana.com/dtjyx/5667.html
- 上一篇文章: ldquo月亮船rdquo的启示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