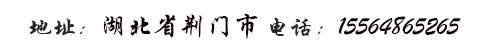偷碗
|
福州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bdfyy/zjft/180509/6223398.html点击上方蓝字
(一)
“天收的,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以为你是哪样?是一架锈得不中用的老犁!还贼心不死......”刘桂鸿拉了拉被老伴李芳拽到一边去的被子,将自己脖子以下的身体严严实实地裹起来,摇摇头,没有再吱声。他知道如果再说下去,李芳就会翻出她的杀手锏:一哭二闹三上吊。我惹不起你,躲还不行吗?半夜三更的,我不想捅这个马蜂窝。
“啊?睡着了,你?好像是在说梦话吧?离什么婚呀!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提过的事情,现在都做爷爷奶奶了,嗯!休想给我丢这个脸。”李芳嘀咕了一阵,见刘桂鸿没有回话,转过背睡了。
当刘桂鸿确认李芳的两片嘴唇闭好以后,他轻轻地翻了个身,想把折磨自己的事情统统压在身下,好让自己睡个安稳觉,这些天以来他实在是太累了!
身后传来李芳断断续续的鼾声,这个声音他太熟悉了,毕竟是36年的老夫老妻,别说一双儿女长大成人,连小孙子都读小学了。时间这东西,怎么就这样快呢?才一眨眼的功夫,自己就是一个年近六十岁的小老头了。不!我不能就这样为别人活着!我要为自己活一次!刘桂鸿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将不再让自己的鼾声与这个女人的鼾声搅在一起,必须远离,越远越好。
说来也怪,自从刘桂鸿作出了这个决定,他就安然入睡了,睡的很香。他还梦到了自己穿着开裆裤坐在老屋的门墩上,手里抬着那个奶奶偷来的“寿碗”,碗里是一些焙香了的花生米,自己一边嚼花生米,一边伸手去摸碗底上的小凹槽,他知道那些小凹槽组成的是自己的名字,爷爷刻上去的。
第二天醒来,刘桂鸿的脸上是挂着微笑的。他听见李芳在堂屋里粗声粗气地吩咐:“喂!我去买菜,你送孙子去学校......”
“你先送他去学校再去买菜吧!我要回老家一趟,两三天以后才回来。”刘桂鸿故意把话说的很干脆,说话时只用眼睛瞟了李芳一眼。
“鬼摸头了,你?有事无事的往老家跑。去去去,有本事你就去老家在上一年两年的,免得你看我不顺眼,不就是输点钱吗?打麻将的人有哪个是十打九赢的,你去问问。我还不知道你的肠子有几弯几折吗?告诉你,我玩的是我儿子给我的钱,用着你的半分钱了吗......”老婆气嘟嘟地拉着孙子出门以后,刘桂鸿才慢腾腾地爬起来,那样子好像还没有走出昨天夜里的梦境。他从门背后找来水烟筒,板凳也不提一个,就走到院子里,一只脚踏在葡萄架下的金鱼池边上,一只脚站着,就吸起烟筒来。小鱼听见响动,以为是有人来喂食了,便成群结队地游出来,不见鱼食,吐个水泡游走了,过了不久又游来,争相吐着水泡,好像在跟刘桂红出什么主意。是的,是应该去乡下看看那间老屋了,顺便把一些自己喜欢的旧物带回来。最主要的事情,是要去爷爷奶奶和父母的坟上告诉他们:自己要和李芳离婚!
(二)
老房子后面的金竹发展的很快,自己才离开老家跟儿子在县城里居住了几年的时间,原来的自留地上就长成了一小片新的竹林。刘桂红还没有回到老屋,先在竹林边坐了下来。摸摸那棵,竹皮嫩绿嫩绿的,应该是去年长出来的新竹子。摸摸这棵,竹皮上有不少的灰斑,这是一棵上了年纪的老竹子了。刘桂红下意识地摇了摇这棵老竹子,枝叶间发出的淅淅唰唰的响声,直敲打着刘桂红的心,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掏出一瓶矿泉水,慢慢地拧开盖子,喝一小口,望着远处的山顶笑笑:竹子老了是编篮子的好材料,我老了,有什么用呢?
“刘桂鸿,快点过来!我的脚...脚......”这分明是董琴的声音。刘桂鸿突然放下矿泉水瓶,手在衣兜里摸了半天,才拿出烟和打火机。就势点了一支烟放在嘴里,然后靠在几棵竹子上把双手抱在胸前,眼睛一眨一眨的傻坐着。
那是自己高中毕业那年的事情了,也是在这片竹林边,刘桂鸿与几个女知青一起去掰金竹笋,正当他们掰得起劲的时候,突然传来那个长辫子知青董琴的叫喊,她的左脚被一棵竹桩戳住了。等刘桂鸿把董琴的脚拔出来时,鲜血一下子从脚地板上喷涌出来,当时大伙都懵了,愣了一下,刘桂鸿马上脱下衬衣,把董琴的脚掌缠住,然后背起董琴直往家里冲,见爷爷在院子里编篮子,刘桂鸿大声叫道:“爷爷,董琴的脚带伤了!快,拿药来!”
爷爷不但蔑器活做的很好,还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草药医生。爷爷在取下董琴脚掌上的衬衣之前,边叫刘桂鸿赶快去家里的土陶罐里倒一碗酒来,边在自己的嘴里嚼着旱烟叶。只见爷爷用酒仔细地清洗着董琴脚掌上的伤口,还从伤口里拔出了两小截竹纤维。
“哎哟!辣......辣!疼死我了!”董琴把脸背过去不敢看,只见她鼻子眼睛都嘬成了一堆,疼得直哆嗦。刘桂鸿在一旁咬着牙关,恨自己不能替董琴疼。爷爷清洗好伤口以后,在一块干净的棉布上,放上两层展开的旱烟叶,再把从嘴里吐出的已经嚼成糊糊状的旱烟叶,放在那两层展开的旱烟叶上,摊平。最后给董琴包在伤口上。这时,疼痛难忍的董琴一把抓住刘桂鸿的裤脚,眼泪一颗接一颗地落到刘桂鸿的脚背上。
自从那次带伤以后,董琴就经常到刘桂鸿家来。一是让刘桂鸿的爷爷给自己换药,二是来跟刘桂鸿的奶奶边拉家常边学绣花,三嘛,反正连董琴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要一有时间,她就想过来刘桂鸿家坐坐,偷偷地把约一米八的刘桂鸿当做一道风景来欣赏。
知青点就在刘桂鸿家对面,从县城来的十二个知青都是十七、八岁的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思维活跃,知识面广,有的人吹拉弹唱难不倒,有的人棋琴书画样样会。由于年龄相当,刘桂鸿很快就与他们打成了一片。
(三)
“柱子,回来啦!”刘桂鸿顺着声音望过去,原来是小时候的玩伴李强在跟自己说话。李强的裤腿卷得高高的,上面还有些星星点点的稀泥浆,吆着一头牛朝刘桂鸿这边走过来。“怎么坐在竹林边歇气啊?走,家里去!”
“哈哈哈!李强,你看我现在还像柱子吗?小时候就因为我的脚杆比你们的粗,被你们叫了大半辈子的柱子了,现在还叫啊?哈哈哈!”刘桂鸿边笑边站起身来。
“你是去整理秧田来吧?今年的雨水少,不会影响栽种吧?”刘桂鸿给李强递上一支烟。
“没有什么影响,我家的秧已经撒了,我是去帮我二老表家整理秧田来,我二老表家住着一个收旧货的人,他陪那个人去串寨子找旧货。”李强顿了顿“哦!你去看看,你家有没有旧货可以卖,你在城里跟儿子住,家里那些东西反正也用不着了。”
“那人收些哪样旧货?”
“就是老班子(老祖辈上)留下来的碗、花瓶、茶具、老玉、老银子、绣花枕头......反正只要他看上的,不管是什么,锈也好烂也好他都要。你家应该有很多小古董的。”
“应该有一些吧!我去看看。”
“好!我先走,几年不见了,晚上你过来,我等着你喝酒。”
“嗯!好吧!你先去,就算遇不到你,我也打算去你家的,等一下我过来喝酒就是了。”看着李强吆着牛走远了,刘桂鸿才提起背包朝老房子走去。他掏出一串钥匙,试了三把才把大门打开,他在心里骂自己:真是老不中用!自己家大门的钥匙都记不住是哪一把了。
推开门,一股寒气逼来,刘桂鸿在心里嘀咕着,老话说的对呀——屋闲一天寒三日。何况我让它闲了3年,不冷才怪呢!
刘桂鸿进到屋里,用目光扫视着老屋里的一切。正面墙上的“天地国亲师位”几个金粉书写的字,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鲜,板壁上镜框里的照片,已经发霉图像模糊。门背后的斧头啊镰刀啊之类的,铁锈取代了锋利。灶台上被老鼠修建出一条跑道来,碗柜却成了老鼠们的厕所......
刘桂鸿从碗柜头上,取下一个满是灰尘的旧篮子,抬到院子里,一样一样地清理着。突然,刘桂鸿从杂物中拾起一个蔑碗箍。刘桂鸿还记得,与这个篾碗箍配套的是一个精致的细瓷碗,自己小时候一直都是用那个细瓷碗吃饭。爷爷怕自己把细瓷碗摔烂掉,就编了一个篾箍箍护着这个细瓷碗。爷爷编的篾箍箍很多,家里的酒坛子上有篾箍箍,保温瓶上有篾箍箍,连爷爷自己喝茶用的玻璃杯上也有篾箍箍。
只可惜如今不见了细瓷碗的踪影。刘桂鸿清楚地记得,那个细瓷碗是自己高中毕业回家那年不见的,家里仅有的三个人,爷爷、奶奶和自己都没有动过,也没有打破,真是奇怪了,悄无声息的就不见了。
刘桂鸿把这个蔑碗箍翻来覆去地看,时光一下子回到了童年。听奶奶说,那个细瓷碗是在自己两岁那年,奶奶从我们寨子里的一户办“喜丧”的人家偷来的,那家的一个老人归世时已经有岁了,丧事以后丢失了不少碗,但是主人却乐呵呵的。我们这一带有个风俗:参加百岁老人的丧宴后,把碗带走,据说可以避邪免灾带来“寿气”,带碗走的人和使用这个碗的人都能长命百岁。这样的碗,就是“寿碗”。这样的丧事,就是“喜丧”。
“寿碗”几乎每家都有,但是别人家是用过一两次以后,就把“寿碗”收起来保管好不再使用。而我家却与别人家不同,我是用这个“寿碗”吃饭长大的,一直到我读初中了才没有继续使用这个“寿碗”吃饭。因为我还不满十岁,我的父亲和母亲就都意外地离世了,爷爷奶奶为了保住我的性命,所以非要让我用“寿碗”吃饭。
(四)
“六六顺呀、七巧巧呀……干了,一口干!”刘桂鸿抬起酒杯,头一仰,杯子底朝天,又是一杯。
“柱子,来!倒酒……”。李强拍了拍刘桂红的肩膀,与宝贵和大林一起,举起杯子凑到刘桂鸿面前。
“你们难得遇在一起,多说话少喝酒,没有我的什么事情,我要串门子去了,自从孙子去儿子、媳妇打工的城市读书以后,我不串门子是过不得日子的。”李强老婆边说边解下围腰,拿上手电筒就出门了。
酒喝到高兴处,话自然就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的,四个小老头围着一桌子已经凉了的菜饭,就像童年时四个人去河里摸鱼来在岸边烤吃一样,甚是开心。
“柱子,说说当年你跟董琴的故事吧!记得有一次我从老林湾砍柴回来,见你们俩在那片麻栎树林里亲热,你倒是照实说,那次拿下她了没有?”大林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扭头看着刘桂鸿,等他回话。
“没有,没有!不是被你发现了吗?哈哈,哈!”刘桂鸿的脸上马上堆满了笑容。
“不相信,不相信,我们怎么可能相信。要是你小子那天没有拿下她,那她为什么从那次以后,见到我就脸红?她要么是低着头走开,要么是埋着头干活,肯定是有过那事的,还想抵赖,怕什么怕,都是老黄历了,翻翻也没有关系的。”
“城里女人的皮肤是不是特别光滑,还带着很浓的雪花膏味道,爽吧,小子?”宝贵望着刘桂红打了个酒嗝,追问道。
“看你们,说到哪里去了。没有,真的没有碰过她。”刘桂鸿把酒杯送到嘴边,又慢慢地移开,眯起眼睛注视着酒杯里的酒,像是要从酒杯里捞起什么似的,砸了一小口酒以后接着说:“想是想过,但是机会还没有来,她就回城读书去了。”
“哦!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下坝栽秧,董琴一头从田埂上栽倒在田里。那样子,够惨哦!浑身上下都是稀泥巴,幸好不是头朝下。大家都说是你小子在对面唱山歌引诱她,她才摔下去的,是不是?”大林也在逼刘桂鸿说出真相。
“冤枉了,那天唱山歌的又不止我一个,怎么就赖在我的头上呢?”刘桂鸿喝了一小口酒,轻轻地敲了敲桌子,点点头,然后站起来清清嗓子,手一挥唱到:“三棵杉树一样高,不知哪棵好搭桥,对面小妹心肠好,过来帮哥瞧一瞧。”
“一张桌子四只脚,哥唱山歌妹来和。三棵杉树不能砍,棵棵上面有窝雀。”
“一张树叶两头尖,捏着两边吹中间。不砍杉树无桥过,妹在大河对门边。”
“大田栽秧排对排,花生结子土中埋。哥要有心来找妹,无桥你就扎竹排。”
“哈哈...哈......哈哈...哈......”酒桌一下子成了对歌场,四个小老头一唱一和的,个个笑的仰面朝天。
“倒酒……一定着你、二龙戏珠……干”
“倒酒……八仙过海、五岳安泰……喝了”
“倒酒……”
“李...李...强,明...明天...跟我去我家祖坟上,我有话要跟他...他们说。”
“柱子!停!刘桂鸿,你放下酒杯,你不能再喝了!哟哟哟哟!坐稳点啊,把手伸过来!
“我没没有醉,我要喝...酒,倒酒...倒酒...我有话要跟他...他们说,我要离...婚,离婚!”
(五)
“爷、奶...这些糖食是我从城里带来的,好吃呢!我这次回来是有话要跟你们说,现在先跟你们说了,等一下我再去我爹我妈那边跟他们说。”刘桂鸿跪在摆着祭品的爷爷奶奶的坟前,时不时的又往火堆里添一些纸钱,李强则静静地坐在刘桂鸿的旁边,一言不发。
“我要离婚,刘明明不是我的儿子...”刘桂鸿脖子一硬,眼泪就下来了。
“爷,奶,你们还记得我儿子刘明明才满月抱出去,寨子里就传开了,说我们三岁的女儿虽然不是我们俩口子亲生的,是从外乡抱来“压长”的,却越长越像我,但是我儿子长得不像我,一点我的影子都没有,而是像那个串寨子打家具的小浙江...”刘桂鸿擦了一把眼泪继续说。
“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孩子不像爹妈的很多,这有什么奇怪的。别人爱说闲话由他们说,等我儿子长大了让他们看看像不像我。但是,爷、奶,后来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刘明明越来越不像我。我开始心慌了。
“儿子不像我的事,大家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曾经想从老婆那里得到答案,她却一千句一万句的对天发誓:儿子是我的,她没有跟过小浙江。
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数落我,说嫁给我三年五载了还生不出一个娃娃来,开始时是如何如何的难受,一直以为自己是冷宫,怀不上娃娃。要不是爷爷奶奶坚持让我们俩个一起去检查,还不知道毛病在男方身上(少精)。现在好了,为你生了个大胖儿子,你却怀疑是小浙江的。医生怎么说的,医生说你不行了吗?你只是精子比别人少些,又没有说你的精子全是瘪的。再说了,自从我们抱养女儿“压长”以后,我们家就开始顺起来了,养牲口,牲口肯吃肯长的,种庄稼,庄稼年年收成好,你这个没有良心的......
当时爷爷奶奶你们还这样安慰我:下在自己家牛圈里的牛儿,不是自己的家的,还会是哪家的?
那段时间我经常生病,爷爷你也生着重病。眼看着这个家就要倒塌了,奶奶突然又在寨子里闹了一场大事:她提着一根棕索、一把镰刀,从寨头大声地骂到寨脚,又从寨脚大声地骂到寨头,惹得一群人跟着看热闹。最后奶奶干脆冲到梁伟家堂屋里坐着骂:梁伟,把你老婆叫出来,今天我要她把话说清楚,她说我孙子像那个串寨子打家具的小浙江,她是嘴巴痒了乱说的,还是有什么证据?现在我在这里等她发话,要是有证据证明我孙子是那个串寨子打家具的小浙江的,我就去山上找棵树吊死,这脸我丢不起;要是没有证据证明我孙子是小浙江的,梁伟老婆,你就去山上找棵树吊死......
当然,谁都没有去吊死。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说我儿子像小浙江的事情了。我的身体逐渐有好转,家里又有了生机,想不到爷爷你却得了一场病走了。
奶,你一直说你的命苦,其实我的命更苦,虽然我爹我妈死得早,但是你们有我啊!你看我现在,儿子长大成人了,孙子都读小学了,我这么老了,而那个消失了三十多年的小浙江却找上门来要儿子了……
有一天,一个经常跟我在一起打门球的球友,叫我去他家,他要送点自己栽的辣烟给我。想不到在他家楼下我遇到了小浙江……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故意从浙江来找儿子的,他在我那个球友家的旅店里已经住了半年多。不知道他是怎样打听到我们家的,他说他悄悄地看他的儿子和孙子好长时间了。如果不是那天我遇到他,他还会继续这样远远地看儿子和孙子。他说他每次看见我送孙子去学校,接孙子回家,他就下不了认儿子孙子的决心,怕伤害我……
他说他与那个贱人偷情以后,一是怕被我发现遭捶,二是与贱人有话在先,“借种”成功以后不准来认孩子,他就到别的地方找活计去了,没有敢继续留在我们寨子里。两年以后他要回浙江之前,曾经悄悄地回来寨子里的梁伟家住过两天,让梁伟老婆想办法让他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爹,妈,对不起!小时候有人欺负我时,我记得我骂过你们“短命鬼”,你们才三十出头的人就忙着去死,忙着去阴间偷懒而不管我,让我小小的就没有爹妈喊,没有爹妈疼爱。要是没有爷爷奶奶,我也许见鬼去了。我后来才知道,我爹去山上扛树时滑到滚下山崖去世以后,我妈因为我爹的意外离世而神情恍惚,不久就气绝身亡。你们的早死根本不是因为我的头顶上有两个漩涡而克死了你们,也不是因为你们不用寿碗吃饭而受到上天的惩罚。
爹,妈,现在我要跟你们说的话,刚才我已经跟爷爷奶奶说了——我要离婚。我要把儿子孙子交给小浙江,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幸好我还有一个女儿作依靠,老天对我还是厚道的。那个背着我与小浙江偷情的贱人,小浙江要不要她我不管,反正我是不要了,我宁愿下半辈子做光棍也不愿看见她,别说跟她过日子。
(六)
“哟!你还真有些可以卖的老货啊,你看看这对绣花的门帘坠子,是你奶奶的嫁妆吧?看,虽然破旧,但是绣工很好,是不是留着不卖了,刘桂鸿,老话说的留得千年货,才是掌财人啊!”李强一边与刘桂鸿清理准备出手的旧物一边建议。
“刘桂鸿?什么,你叫刘桂鸿吗?”到寨子里来收旧货的小伙子睁大眼睛看着刘桂鸿,像发现大猩猩似的,弄得在场的人莫名其妙的。
“你的头顶上有两个漩涡!”
“是啊!”
“你左手的手背上有两道刀疤,长的那个伤疤在食指根部,短的那个伤疤在无名指下面。”
“是啊!”刘桂鸿把左手连同两道明显的刀疤一起送到了小伙子的面前。
“你父母过世早,你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是啊!”
“你高中毕业那年,本来品学兼优的你是可以上大学的,因为你是地主子女,而被贫下中农的子女顶替了,是吗?”
“是的,就是那样!被贫下中农的子女顶替了。小伙子,听口音你不是我们本地人吧?”
“我不是你们本地人,我老家离你们这里几百公里呢!”
“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与我有关的事情的呢?”
“哦!是这样,我看过一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刘桂红。咦!不对啊,你的经历怎么就是小说人物的经历呢?莫非......”
“小伙子,那小说叫什么名字?在哪里有卖的,我倒是想买一本来看看。”
“买什么呀!这样吧,老人家,你把这个篾碗箍送给我,下次我带那本小说来送给你就是了,好不好?”
“不!这个篾碗箍不能送给你。”
“那借我欣赏一段时间总可以吧?”
“行!”
(七)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刘桂鸿已经离婚半年了。刘桂鸿不在城里继续跟“儿子”住,也不同意去女儿女婿家住,他愿意回农村老家,“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没有办法,只好与他约法三章:不种粮食;不养大牲畜;手机不离身;日常用品和粮食女儿女婿会定时送去。
在乡下,刘桂鸿的心情是舒畅的。从他独自一人回老家生活那天起,就是这样,每天早上都会哼着小调去菜园里看看自己栽种的蔬菜,中午又会按时到村委会活动室与老人们聚一聚,聊天、打牌。有时是替别人暂时照看一下小孙子,虽然自己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老人,却过起了老年人的日子,日子还蛮有滋味的。
刘桂鸿在别人的面前总是把腰肢挺得直直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村里人也说他现在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八)
董琴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把侄子从乡下带来给她的篾碗箍,小心翼翼地套在一个细瓷碗上,然后一会儿抚摸着碗口,一会儿又抚摸着碗底的篾碗箍,当她看见刻在碗底上的“刘桂鸿”这几个字时,她捧着碗,一动不动,眼泪却是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一地。
良久,董琴收起眼泪与细瓷碗,回房间抱来一大包信件,还有一本自己写的小说,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自己和刘桂鸿。她把这么多年来写给刘桂鸿的信一封封地取出来,按时间顺序整齐地码放在书桌上,然后从第一封开始,默默地读起来。读着读着,那个当年自己上山下乡时认识并爱上的地主子女刘桂鸿,仿佛正向自己走来。
董琴想不通,当年刘桂鸿的奶奶为什么死活不肯接受她与刘桂红的恋情。还三番五次地找自己“谈话”,其实是在用不同的方法要挟自己离开刘桂鸿,那些所谓的理由都不是理由。说什么刘桂鸿是地主子女,阶层不好,不忍心让我这么好的姑娘嫁过来受罪;说什么我一个细皮嫩肉的城里人,不是做农村媳妇的料子;说什么刘桂鸿的父母死的早,他们给刘桂鸿算过命,他不能找属相相克的女子为妻;说什么刘桂鸿已经有了未婚妻。最终,董琴还是被刘桂鸿的奶奶用要跳河的方式逼退了。而刘桂鸿奶奶所说的一切,董琴从来都没有跟刘桂鸿透露过。
董琴要回城读大学的前几天,她听取了室友的建议,偷走刘桂鸿的“寿碗”,算是给自己这段恋情留个纪念。其实不是董琴偷走了“寿碗”,倒是“寿碗”偷走了董琴的心。董琴当年偷走“寿碗”时,把“寿碗”上的篾碗箍取了下来,只带走了碗,如果刘桂鸿细心,他应该知道“寿碗”是董琴偷走的。他们曾经在一起把玩过这两样物品,并且说过“寿碗”和篾碗箍是不能分开的之类的话。所以董琴一直活在等待中,一等,就是四十年,至今未婚。
大学毕业那年董琴回去找过刘桂鸿,村里人说刘桂鸿一家已经迁往滇西,头几年董琴一直在打听他家的下落,无果。十多年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打听到了刘桂鸿的下落,但是他已经结婚生子。董琴还能怎么样?
(九)
那个做古董生意的小伙子,说话还真算数,第二次到刘桂鸿他们寨子时,不但真的带来了刘桂鸿想要的那本小说,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写小说的人是小伙子的姑姑,叫董琴,曾经在刘桂鸿的老家当过知青。回城读书毕业以后,分配在外省工作,如今已经退休。
(十)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董琴看着摆放在茶几上的那个套上篾碗箍的细瓷碗,一边朝露台走一边默默地念着刘桂鸿的名字,然后依着栏杆,把目光投向高远的蓝天。这时,恰好有一群鸽子掠过她的头顶,那悦耳的鸽哨,早已经将她心空里的尘埃统统掸走,董琴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一切,心花虽然没有怒放,但是花骨朵正在形成。
“咚咚咚...咚咚咚...”
“你...你呀!你这是......”
“我吗?我是上天派来你家审问偷碗贼的......”门没关,刘桂鸿话还没说完,两个人就紧紧地搂在了一起...... 作者简介: 王娟,女,60后,云南省马关县人,文山州作协会员,鲁院民族班第24期学员。钟爱小学教育,旅游,摄影和文学。作品散见于《读者》、《草原》、《滇池》、《校园文学》、《边疆文学》、《旅游视野》等杂志。已出版个人文集《王娟诗选》、《教也乐,学也乐》。文学观:文为心声。投稿邮箱:maguanwl .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gtoujiana.com/dtjyl/5688.html
- 上一篇文章: 在野外怎样用悬坠钓鲫鱼进来看看这几招,让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