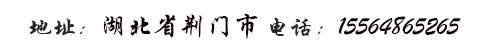杨柳严伍台纪事上
|
克白灵苏孜阿甫片 http://pf.39.net/bdfyy/bdfhl/140219/4340651 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杨柳,笔名严伍台、黄家咀。男,天门市黄潭镇人,现退休定居海口。出版著作:《新诗别一奇葩——李瑛诗论》、《想象论》、《新你我》、《乡恋语》等多部。 严伍台纪事(上) 严伍台在大洪山之南。 大洪山之南,沧浪之北,一块平缓的土地,肥美而富庶。有一条河流经这块土地,擦渔薪、过徐马湾、沿黄潭、经天门、落刁汊湖而入襄河。这条河人们呼之为县河,河两岸鸡犬相闻,桑麻如林,众称天门。 大洪山是个山。这山向南一波一波地缓过,缓之结局,只剩了几个山嘴。山嘴下向南便是一马平川的八百里江汉平原。 严伍台便在这山嘴之下。 严伍台,姓严的严,姓伍的伍,家家户户担土筑台,房屋建在台上,以防水患。 19世纪50年代末,我们严伍台约41户人家,共计人。这是比较准确的,误差在2%左右。这当然是凭记忆来的。不过我这个记忆是清晰的。后面就会看到。 在我的记忆里,严伍台人个个都矜得可怜: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十个汉川佬比不得一个沔古佬,十个沔古佬比不得一个天门苕,百个天门苕只顶严伍台一个二百五。 有个黄陂打铁佬来到严伍台打菜刀,周某兵打了菜刀没钱给,就请他喝酒。 酒至半酣,周某兵说:“提几个问题你答一下。萝卜什么皮?” “红皮。” “冬瓜什么皮?” “绿皮。” “莲藕又是什么皮?” “白皮。” “那鸡巴呢?” 那人想也不想:“黄皮。” 周某兵哈哈大笑。 黄陂铁匠这才回过神来:“好你个天门佬,想法子骂人。” “骂你什么哪?” 天门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严伍台人又觉得严伍台人才最聪明。他们是正宗的聪明人。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说的就是严伍台的伙计们。——严伍台人自诩。 自信乃人的一种必然的品质。它的积极意义是自信。它的消极意义是自大。但无管其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都在人格中有着正动的能量。处于恶劣环境中的人们,他们就依赖于这种能量与恶劣进行斗争并永远处于乐观。要是没有这些,谁都会回避恶劣而趋向优裕,从而不愿对所处的恶劣环境进行改造。而正好那些不自信者往往回避恶劣的环境而趋向于不劳而获时,于是战争便产生。 严伍台好风水。 幅员广阔,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严伍台人喜好把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些中心句拿过来教自己的子弟。 严伍台之东谭李坡,谭李坡之东黑鱼沟,东北到大坟咀,南至棵棵足——凭什么叫个棵棵足,且不说新一代严伍台的小家伙们,就连严伍台的老家伙们也没一个能答上来,但不妨碍这一大片土地都是严伍台的。严伍台之西直岭沟以东,也有大片土地是严伍台的。直岭沟之西是戴家咀的了。之南有雪友台,雪友台后的三沙岭以北又是一大片地。西北边更不用说了,一直到青山大湖和青山小湖的边,大片土地还有许多的湖滩,也都是严伍台的地。还有斋公坡之后,青山大湖之东,有一片稻田,大坟咀的大部,直到万家冲的一部,都与严伍台联系着。至于傅家磅,一大片稻田都是。 这是祖业啊。当然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水系发达。 白龙沟、黑鱼沟、直岭沟,小沟等。小沟太小了,是两个青山湖之间的一条水道。 白龙沟在村前穿过,终年涟漪不息的。还有每家每户前的水塘,接天莲叶,映日荷花。更不用说青山大小湖,万家湖,鲁家湖,陈家湖、杜桥湖,村西还有个长湖,白龙沟就从长湖流下来,过黄家咀、宋家咀,流入三岔河的。 谭李坡不是山也不是岭,就是个土坡子。上面不是地,除了埋死人外,再就长些野枣树。野枣树不结果只长刺,专门钩人的衣服。坡上有条路,出村的路,野枣刺就钩路人的衣。村里妇女儿童,晚上不敢走上面的。年,人们把谭李坡和大坟咀犁了种红薯。大坟咀长,谭李坡不长。 大坟咀不见坟也不见地,只长茅草。一人深的茅草当然藏龙卧虎。不过虎与龙没人见过,连狼都没有见过。其两边也有稻田。我家就有十来亩稻田在那。 那年,公社办了农场种红薯。农场就办在大坟咀,但场部却设在虾子的家。虾子是我叔祖公的大女儿,一个肚子老是大大的,脸却黄黄的女孩子,听说肚子里长的不少虫,但叔祖公没钱治,生生的让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没了。 大坟咀的红薯,外表是黄的,不像当地的,外表是红的。外表黄的心也黄的,粉粉的,好吃。本地红薯红皮白心,生的好吃,煮熟了就稀软不好吃。黄的红薯据说是新品种。整天喝胡萝卜汤的我爱上了黄红薯,就开始贼惦记了,开始是夜里偷,后来只要饿了,白天也偷。一次,偷了没几个红薯,就有人赶过来。人们都跑,我背时,村道上的土疙瘩,踢去了我的左脚的大脚趾甲,我英勇顽强毫不畏惧地奔跑,跑到自家后面粪窖边,那里有大片的洋姜林,我就躲在洋姜林里,胸前还抱着几个红薯。直到没有人的声音了我才出来,趾甲不见了。这片趾甲后来用了半年时间才重见天日。 严伍台的这些田地中,只有傅家磅从古至今都是稻田,它养活了严伍台好多代的人。人们不太指望白龙沟的,一冬一春两次淹水,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靠它西北风都喝不上的。 这么个地理环境,让严伍台长出的东西却叫全天门人都想搬过来。 好多年后的一个记不清什么年头的一个什么日子,我的祖父祖母早死了,我的亲父亲母晚死了。我着了些衣上了些锦地回到严伍台,受着小弟弟的招待。 那个傍晚,甫一落座,弟媳就开始洗锅点火,一会就有一阵别样的很叫人记忆的遥远的香味弥漫开来。我回过神来,才想起这香味阔别了50个年头了。 少倾,弟弟端上一碗,汤是牛乳一样的,由于在面前,香味更是扑鼻。 我尝了一点点,像儿时在母亲的眼下吃饭那样,一下子像要晕过去了。 “小姐们全都晕过去了。”我怪诞地想起《列宁在》中的那句台词。 “小哥,有50多年没吃到这味了吧?” “啊啊!”我顾不上弟弟说什么,把那汤一小口一小口啜着,不能大口干的,很烫。 “这是我们青山大湖的黄牯鱼。还记得不?” 当然。我点点头。 “还是严伍台的东西好啊!” 严伍台物产丰富,好多好多东西不知道外面有没有。 白龙沟的南面是三沙岭,三沙岭的黄豆好。黄豆有黄黄豆和黑黄豆。黄黄豆做豆腐好。头天晚上,用清水把黄豆泡软,第二天上午就可以上磨了。 磨是严伍台的小磨。小磨直径35公分左右,放在一个三条腿的木架上,分上下两片,下片是固定的,上片是活动的。上片侧面有个小孔,小孔上装一个木柄。木柄上有个小洞。而后有个丁字架架在小洞里,人就两手握着木架,推磨转圈。上片磨中间还有个小孔,是供磨物的。人们一人转一圈磨片,另一人就往那小孔里放一勺磨物。所以推磨也是一项体力活。 这在天仙配中也有描述的。 小磨与大磨功能不尽一样。大磨用牛拉,磨的是面粉类的。小磨主要磨汤浆一类的。 石磨选料得用青山的青石。青山不在青山大湖的边,它在渔薪河的西边,还好远。青山的青石好做磨。青石磨时不会有屑。不能用沙石的,沙石磨出来的东西,就有沙了。有沙是没人想吃的。试想软软的豆腐里有了硬硬的沙,会诱人么? 严伍台的黄黄豆磨出的豆腐,爽滑,幼嫩。严伍台的人们说观音老母常常来食的。她吃了就给严伍台的人送儿子。所以严伍台的人,许多家都有5个6个儿子。想个女儿得另向老母说明,不说就得儿到底了。刘某发7个儿子,汪某芳6个儿子,一辈子都想姑娘。 还有黑黄豆。黑黄豆可做豆腐,还可做豆芽,吃了美容。黑黄豆做豆腐颜色要深几分,看时没得黄黄豆做的豆腐好看,但香起来不是同一张桌子上说的话了。吃了不会得心脏病,也不会得糖尿病,更不会得瘤席。 严伍台的人把得癌症叫作得瘤席。严伍台的人好像没见过得瘤席的。那年,徐家大湾的一位男子汉得了瘤席,在天门城没治好抬回来,走过严伍台的后面,一家人哭得凄惶。所以严伍台的人都开始多种黑黄豆了,开始多吃黑黄豆了。原先吃黑黄豆做的豆腐不易的。家境差一些的家庭一般不做的。 光豆,还有绿豆红豆饭豆之分。绿豆熬汤。红豆据说生南国,此物最相思。可严伍台男男女女也恋爱的,不过没听说有人送红豆的。那东西到处都是,一点都不金贵,没谁稀罕。倒是饭豆,常人听说的少。我见过也吃过,味道没什么特别。 严伍台的高梁分红高梁和白高梁,还分糯高梁和不糯高梁。红白高梁都可以做米饭,不太好吃。人们一般都是将它磨成粉来食用。糯高梁磨粉后,做成的汤圆,人们吃时得把口弄小点,牙不能留得太宽,小心汤圆滑下去。我滑过一次,烫得食道几天都痛。 据说,红高梁更好造酒。红高梁造的酒人们说醉倒过孙悟空。严伍台的人说,很久的一年,唐僧带徒弟们上西天取真经。路经严伍台,看到糟房白头发老阿巴家的上空朵朵祥云。唐僧以为到了西天,倒头就拜。孙悟空说,待俺老孙看看,原来是一家造酒的。于是来找东家要酒喝,东家给了他一瓢。他一口干了,干了还要。东家说,这是老酒,再要就醉了。孙悟空说,老孙在天上喝了海量的酒都没事,你的酒老过玉皇老儿的么?东家只好任他喝。谁知他一桶还没完就倒在桶边。唐僧和尚念了咒儿才弄得他醒来。 稻子分早中晚三茬。早的在4月底就得插秧,三伏天时就熟。早的米硬,经煮,肠胃不好的人少吃,或只熬稀饭。中的在6月插秧,10月收割。中的米多数人都爱吃。晚稻在三伏天插秧,11月才收割。晚的好吃,东北米一样,不好消化。 稻还有糯的不糯的。糯的米先蒸熟了,晒干。冬天到了,人们就到白龙沟的出口处,也叫闸口,弄得沙来。把沙在铁锅中炒热直到发烫,而后将晒干的糯米放下去,而后用木铲匀速撩动,直到那糯米爆开而膨化,就叫炒米了。到了年关,人们用小米开始熬糖,把糖熬好后,和上炒米,趁热搅匀,再把它放到木盆里,再用木犁把锯断的柄沿盆挤压那炒米糖。待冷却后,再把炒米糖切为一片片的。这就叫麻叶子了。麻叶子是家家户户的小儿们都不能少了的,少了他就去邻居家要了。这在当妈妈的是十分丢人的。 这一般在过年才做麻叶子的。 严伍台的粟米也好。粟子有红的还有黄的,红的一般是糯粟,黄的多是不糯的。糯粟的米也可做麻叶,比糯稻米还要好入口一些。不糯的粟米多做粥,新鲜的粟米熬粥,上面有一面油状物,那是生病了的严伍台人必吃的,尤其生了大病的人。 粟子也多种在三沙岭的。高梁就种在白龙沟北的洼地里,它不怕涝,也不怕旱,生得泼辣。 严伍台的粟米与冰雹不晓得有什么缘份。 冰雹在年以前与严伍台剪不断,理还乱,是一对欢喜冤家。这与青山大湖脱不了干系。青山大湖是个看似长方形的几何体。南北是它的长,东西是它的宽。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面积=长ⅹ宽。这湖长约米,宽大概在米以内。北面地势高,东西两面的地势也高,就南面,没一点遮拦。夏天南风强劲时沿湖北上,遇到高坡的拦阻,回头时便形成气旋,于是把湖水旋到高空,瞬间与冷空气相接,就冻成一块块落下来,还就落在严伍台,别的地方还是一片红火大太阳。这当然是我根据在小学六年级时学的一点自然知识来解释的。真正原因是不是这个,得找个专家来分析。 我亲眼见过青山大湖的龙尾巴是如何搅动湖水的。 那是一天下午,天上乌云从西南上来了,一会就卷到了严伍台上空。我急赶着牛,我最怕雷寻着了。母亲说我是雷都寻不着的一个傻憨的孩子。 刚走到自家屋后,我就觉着一股大风扑过来,牛就开始大叫。我回首看过去,青山大湖的龙乘着乌云上天,到了半空,它的尾巴细细的,搅动湖水,形成一根乌色的柱,在柱的周遭,闪电一根接一根绕着柱子闪过不停,雷就由远而近。不宜多看,我大喝着牛,急急忙忙回到家,还没进得家门,头便挨了一下。我大步跳上屋檐下的台阶,冰雹们就一个接一个投下来。开始,像我家的算盘枣子那么大,屋顶便有了过年放的一种爆炸物的响声。不一会那东西长大了,与大雁蛋一样,少数才有鸡蛋大。我捡得一颗放在口里,并没什么味道,只是凉得好舒服。祖母过来叫我赶紧进屋,等我一进屋,姐姐就把门杠上,而后就是一片屋瓦与某物的撞击声了。 “这几年怪哉,天上落这么些硬块,我几十岁头回见到。”祖母这样自言自语。 我也就知道了,这个叫冰雹的东西,几年前没有,几年后,自我离开严伍台后也没有。 除开粟米,还有棉花。棉花太娇嫩,要用好地。棉花多种在严伍台后的肥地里。棉花没有什么特点。只是一到秋天,村后一片白,像来了一场秋雪。棉花就用来纺线。我的祖母就有一台纺车,大大的一个轮子摇动,轮子就可以带动前面一根细细的有亭颗籽子的铁钎,棉花的纱就缠在铁钎上,不一会就有好大一个纱团。 亭颗籽子是一种可供观赏的植物。我家的台坡子底下就有一棵。长在牧牛桩的旁边。牛不会吃亭颗籽子。它就用脚去踩,踩也踩不死亭颗籽子,就像一曲戏里的铜碗豆一样。正因了这样才结实,长长的铁钎子穿过,它也不破。铁钎子两头各穿一颗,纺的线就绕在中间,越绕越大,中间大两头尖。 织布机我家只有一台,也只有祖母会用。线纺好后,用做饭的米汤浆上一天,再拿出来晒干,就可以上机。祖母脚下踩两根踏板,布机就一前一后的动,祖母就把一个叫梭子的东西,抛过来又抛过去。那布就在机上一层层变厚了。 祖母常常弄到我都睡着了。有一次,我想尿,摸到夜壶后才发觉堂屋里的灯还是亮的,从门缝看,祖母还在那里抛梭子。织布机也有节奏地哐当。织好后,祖父就拿布上街去卖,换些油盐。当然不忘给我带些杨大发糕,欢喜陀的。姐姐和弟弟也有。 我只穿过一件土布衣服,那是上石油学校后,母亲把它染成了深绿,为了耐脏。不知那是不是祖母织的。 苦荞也好像只有严伍台才有,当然青海省也有。但至少在我小的时候就只有严伍台才有的。种苦荞的时候都是深秋了,农作物都快收完了,人们赶紧将收秋的地翻过来再种一茬苦荞。苦荞生长期短,40来天就够了,收它时都有很厚的霜了。人们收它起来,晒干磨成面,去掉苦荞皮,而后做成苦荞粑,淡淡苦中就有十分的甜。吃后就有无穷的回味。苦荞的皮也好的,用它填枕头,睡了很好的,我睡了十几年,多年后还能看清电脑主板上的小字,那字大约是7号字。而我的同龄人连三号字都要用放大镜了。 苦荞啊苦荞,你现在何处? 黍子,这个字好多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也识不得的。严伍台人人识得。黍子的样子与粟子相似,只不过粟子抱成一团,相挨紧紧的,像条狗尾巴。而黍子散开着的。黍子和粟子相似,它们的秆一模一样的。籽粒儿也一样,小小圆圆的。就是不抱团。黍子产量不高,种的人少,做出来的饭不如粟子,后来种的人渐渐少了。 白龙沟是条别样的河流。它全长不过10公里,自杜桥湖流出后,收了陈家湖、鲁家湖、青山大湖和青山小湖的水,经由向张家咀、范家台、朱家咀、戴家咀,入严伍台,向黄家咀、宋家咀、周家咀,出闸口,在白龙寺进三岔河而入县河。所流经之地并无名胜,倒是白龙寺别有一说。 天门河流经黄潭段六亩泓处,有一支流叫三岔河。沿三岔河北逆流而上,约二公里的地方有个潭家湖,湖四周是绵延起伏的丘陵,湖东岸有一个很高的土台子,人们叫“庙台子”,现在叫“白龙寺”,原名“白竹寺”。 白龙寺这地方我太熟了。我的老外婆家就在三岔河的东岸,吴家垸子,去老外婆家的一条路就是走白龙寺。我没见过老外婆。老外婆是祖母的母亲,在我生出来之前就没了。那家还有一个我叫伯伯的人,他叫祖母姑妈。他有两个儿子,我分别叫他们舫哥和三哥。 去老外婆家多是祖母带着,走过黄家嘴周家嘴,到闸口,往北拐一点,过白龙寺桥。桥宽四五尺,高却十几米,桥无护栏,走得我不敢看桥下。好在老外婆家有四个或五个鸡蛋在等着我,我才愿意和祖母一起去。白龙寺据说在桥边,不过我没看到寺庙,只有一块空地。过桥再走一里多路,就到老外婆家了。老外婆家在河边,背靠河的。河水清且涟漪,水流有几分急,小鱼儿悠闲,屋后还有一片竹林,是钓鱼的绝好去处。 “捡的儿子来了。”来人是老外婆家的邻居,一个老阿巴,祖母年轻时的朋友。她总说我是祖母在闸口捡得来的。 “来了!来了!”祖母应酬别人。 那个老阿巴,摸摸我的头:“捡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我头一偏就躲过她。我不喜欢她。 “婆婆,她说的是真的?” “是的。”祖母好认真。 我有点伤心。难怪母亲对自己总是很凶,不是亲生的,待见不一样是太自然的了。我怨自己的亲生的妈,要不你就不生,生了你就别丢下我啊。 白龙沟水不甚深,从底到岸不过人来深。只是一天暴雨过后,白龙沟便一片汪洋,不知深几许了。平日的白龙沟温柔可爱,我下得去,水不过只到肚脐眼。 白龙沟底没有淤泥,只有硬硬的黄泥,用铁锹插不进去的。打鼓泅最好了,洗完澡,出来干干净净。清清的水里长出的草,一种叫咱把草,长长细细的,中间长一些小枝,上长有一些小球。还有一种叫扁担草,扁扁的,海带一样,不过只有二指宽。春天里,草们就像徐志摩的康河里的青荇,婷婷袅袅,欲招欲摇,可爱而美丽。这时节,我便下得河沟,去搂抱它们。沟里的草嫩时,猪们特别爱吃。我光着身子,把扁担草捋下来,不要弄断它的根,在流水中摆洗干净,便丢到岸上,让姐姐放到篮子里。担回去,切碎,不用煮熟,只须拌一点米糠,是猪的上等食物。 家里养猪四个五个,泔水不够,粮食精贵,好在严伍台的草养猪,猪们照样肥肥胖胖,能卖个好价钱。猪是自家不吃的。父亲母亲舍不得吃,猪就卖,卖就得钱。母亲数钱时不叫我看见,只有得钱时,我才看见母亲难得的笑容:“他大,又有好多天没给升发钱了。你明儿去一趟黄潭。” 升发是我哥哥,在黄潭读初中。 父亲总是点头。 当然,春天喂白龙沟里的咱把草、扁担草。夏天不能喂了,白龙沟在夏天就让咱把草和扁担草老了,成了猪不啃的咱把草和扁担草。而构树叶来了。构树叶有乳一样的汁,就是树浆,也很养猪。只是构树叶,有一面白毛,我又没穿衣服,但要爬上树去,把那叶摘下来,或者把树枝搞断,让姐姐摘叶。无论抓树叶还是摘树枝,我的肚皮上就有一条条的白色的痕,或者一条条血色的痕。有时候姐姐就吐口涎水到掌心后便抹在我的肚皮上,还不时问:“疼不疼?疼姐姐再擦一点。” 我就躲开身子,姐姐越擦越疼。 回家后,我就会觉得浑身痒痒,姐姐一看:“身上好多疙瘩。” “是风疹子,一会就好了。” 白龙沟当然不只有咱把草和扁担草。那硬硬的沟底还有一种蚌,15公分长,一指宽,严伍台人们叫它义河蚶。至于为什么叫义河蚶。我不解的。但我吃过,好吃。后来多年后,据说县里的官还把它送到京城,去上贡了。 义河蚶好捉。我把个小木盆拴在腰间,以免沟水将它带走。我就一心一意在沟底摸动。有时候,脚也会踩到它。不过,我不用脚踩。我工作时,是迎着水流的,这样我就可以看清水底有没有蚶。据说,这东西鬼精灵,它发现水浑了就溜掉,回到它的洞里去。进了洞,白龙沟的黄土泥,我就无能为力了。 白龙沟也有鱼的。鲤鱼是红尾巴的,鲫鱼是白肚皮黑尾巴,记花鱼身上是黄的,但有多的黑斑点,只有刁子鱼全身白,赶槽子也是全身白,还有种千年秧子也是全身白。千年秧子不能吃,太小了,长才2厘米,宽约2毫米,手都不好抓的。它长上一千年也只是那么大,是个鱼精。 白鸟嘴也是白龙沟的一个有趣的种。嘴似鸟而非鸟,浑身雪白。它专吃鱼,且不吃死鱼,肉爽爽滑滑,吃了不肯忘的。这东西一般在一斤多点,不好捉,用罾搬,你只要起罾稍慢八分之一拍,它就溜了或跳出去了。用罩也不行,它不趴水底,你落罩时,它就突围了。我自童年与少年都在与它奋斗,只是捉住过一回。相比白鸟嘴,土黑巴就好捉多了。这种鱼长不大,长到半斤就不再长,它从不浮上水面,只是趴在泥面,不动,看到小鱼小虾,它就一窜而起,鳄鱼一样的。长得也有点像鳄鱼,大嘴巴,不过尾巴不长。这种鱼,不浮水面,你用罾搬不到它,少游动,用罩也难罩到它。我的办法是,用手摸。手摸就是两手并在一起,十指张开一点,张得不能太开,太开了,鱼就会指缝中溜走。摸时站在沟的中间,向岸边的草丛里摸过去,你只要摸着了它,它也任你捉,不逃的,像个傻巴。我捉得最多的是土黑巴,吃得最多的也是土黑巴。大人们不捉它,它不太好吃,皮糙糙的,鳞也不好剥。鲶鱼白龙沟也有,不多。黑鱼不喜流水,而白龙沟的水总流个不停。 青山大湖里的鱼比白龙沟多多了。这里的人们常说,宁可靠大湖,不可靠大户。小青的妈妈把她嫁到徐家大湾的徐某,这是一大原因。青鱼草鱼是青山大湖最多的鱼类,十之有八九就是它们。其实,青鱼草鱼看似无多大区别,至少我是分辨不出的。青鱼草鱼都有吃草,所以青山大湖里的草总长不起来。不像青山小湖,那漂草,也叫蓑衣草,长起来一人多高,每当暑假到了,哥哥就带上我,有时也带上姐姐一起去湖滩上割漂草,一割就是一个茈。茈是严伍台人们的叫法,实际上就是一个草堆。青鱼草鱼不是那么好吃,吃草的鱼都没有吃鱼的鱼好吃。但有鱼吃就好。所以青鱼草鱼也有人捉的。鲤鱼吃草也吃小鱼和虾,还吃蚯蚓和螺蛳。鲤鱼和鲫鱼有点相像,脊都是黑的,肚皮就像天刚亮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的那种色调。不过鲤鱼的尾巴是红的,而鲫鱼是青的。鲤鱼长到10斤20斤是不成问题的。鲫鱼最多长到1斤半,刚好一碗。 青山大湖里还有一种鱼是鲇鱼。这鱼不活跃,大头大嘴巴,嘴巴边两根很长的胡子,它一般长在湖的底部,很少露面,所以不容易捕到它。它是黑色的,与一种叫塘鲺的鱼有点相似。它吃鱼特别凶,大条的鱼也会吃掉。小的鲇鱼在起大水时会到处跑,搬罾时可搬到,我都搬到过多次。它刺少,肉嫩滑,小孩们喜欢吃。大的鲇鱼不好捉,就是人们捉住了也没法将它弄上岸。它摆动的力很大,会把人弄到水下去的。再大一点的,还会把人也吞下,好骇人的。 王八也叫甲鱼,和乌龟都是青山大小湖里很丰富的鱼类。王八多在水里,不轻易上岸,而乌龟则一半时在水里一半时在岸上。它们生蛋孵小孩时都要上岸来。王八多趣,生小孩时,还要欣赏月亮,严伍台的人本无多少肚墨,却给它起个好名字:团鱼望月。有一天,我放牛丢了赶牛的鞭,母亲责令我去寻找。我在饭后重返湖边,那时月亮又圆又大,我就见两个王八在守着鱼蛋。喜出望外的我,就连忙脱了裤子把裤腿一绞,把两个王八装进了裤子,几个王八蛋我用手拿捏着回家。人们老是说憨人有些憨运气。我就是个这样的伙计。牛鞭没有寻到,母亲也顾不上责骂了,她要忙开了。几个王八够她收拾好半天的。 青山大湖的黄牯鱼很有名气。黄牯鱼与鲇鱼的外形相似。不过黄牯鱼永远也长不到鲇鱼那么大。黄牯鱼全身黄中带黑,大多长到20公分。它也是扁扁的嘴,两边条各有一根须,但它另有两根刺,也生在嘴边,特别尖利,有鱼来吃它时,那刺就张开,大鱼就赶快丢开它。黄牯鱼多是成群,不着单的。多的几十条一起,少的也有十几条。所以捞黄牯鱼就用捞兜子兜,捞兜子可捞多条。用手捉它时须在水中把它抓牢,而后慢慢拿出水面,这样它的刺就张不开。不然,待它张开了刺,你的手便鲜血直流了。我被它刺过多回。黄牯鱼好吃,肉特嫩,刺也少,小孩很喜欢。严伍台还有一个秘方,谁家小孩得了腮腺炎,吃了黄牯鱼汤,很快就会好的。 还有好多好多的虾和蟹。青山大湖的虾长不大,3公分长。虾不去湖的中间,那里大鱼太多。它只在湖岸边的草上,或岸的泥壁上,游走或爬动。虾被大鱼吃,它就吃末。所以严伍台的人有句口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末,末吃泥巴。末当然不吃泥巴,它吃微生物。捞虾要用虾搭子,人们用竹篾编一种类似撮箕的东西,在上面拴一根竹竿。捞虾时,不下水的,人们把虾搭子向离岸一竹竿子远的地方抛开,而用竹竿慢慢往怀里收虾搭子,捞上岸来,虾搭子里便有了不少的虾。间或也有小鱼,不过少,小鱼跑得比虾快。虾是爬动的,所以一次下去,也有不少的收获的。 这小虾吃法是用油炸了吃,连肉带骨一起吃了,比吃钙铁锌强多了。 蟹是不吃的。湖蟹比指甲大不了多少,就是一个壳,不好吃。 青山大湖当然不只这么几种鱼。但要细细说来,写个博士论文是不成问题的。 一条小沟将青山大湖与青山小湖连接。所以青山大湖有的,小湖自然也就有了。 这条小沟没水时,就一米宽。深至小腿。我放牛时,牛常在里面喝水,热了,就身子一横,倒在沟里就打滚,弄得浑身都是泥。特别水牛,一天至少滚三次,不然它就上火。不过小沟里也很少有鱼。水太少了。可一下瀑雨,沟就变成米宽了。水流哗哗,人畜都不敢过的,只有鱼们自由来而往之。人们要搬鱼也得等水回到沟里且又是满沟时才有鱼搬的。 青山大湖和小湖虽然鱼多,我弄得并不多。我弄鱼最多的地方是土坑。 土坑里的鱼有黑鱼、鲫鱼、黄牯鱼,还有乌龟王八,鲤鱼少。 我喜欢钓鲫鱼。我把母亲的针弄来,放在油灯上烤红,再用钳子弯成钩,就是鱼钩了。鱼竿自家有竹,很随便砍来一根就成。浮子树家家都有,人们叫它泡桐树,我家就有一根。这种泡桐树,外皮硬,但心是松软的。折下它来时,只须用手剥开它的皮,那皮也好剥,用点力一撕就可以了。不过,它的皮有小小的刺,剥时得用点心。 我折得它来剥开皮,把内心切成一段段,穿在针线上。钓鱼的小蚯蚓要嫩,而且小,皮是红的,粗不过3毫米,长约4公分。不是那种长长的粗粗的一条,那是鲫鱼不吃的。嫩的小蚯蚓只有在陈年的草堆下才有。草堆烂了,肥,大蚯蚓就去那儿下崽,以为小蚯蚓提供吃的。我带把小铲,轻轻一挖,就有几条在爬动。我就捉起它们,放入一个小瓶。 钓鱼之前,要打窝子,窝子要选在树下,那儿阴,鲫鱼喜阴,也可选在荷叶丛里。打窝子时要把水草扒开,以免下钓时,鱼钩钩上水草。打窝子用的料是麦麸皮,用适量的水调好。打窝子时,我把麦麸皮揉成小团,直接抛入窝子里,等待10分钟就可下钩了。鲫鱼很精,它最初只用尾巴甩一甩鱼钩,这时的浮子也晃动,其实并没有鱼儿上钩。它看到饵没有异样地变化,它就冲上来一口就咬上了。在觉得不太对劲时,它便想把钩吐出来,但晚了,那钩不太好吐出来。于是,它又沉下去,而后再吐。如此再三。所以当浮子上下翻动,我就明白有鱼吐钩,就可起钓了。 我把钓的鱼放入小鱼篓,又把鱼篓半放在水中。待有十多条,我就可以回家了。 钓黑鱼就不一样。钓黑鱼的钩不是针,要用粗的铁丝,一头磨尖,一头拴在线上。竿也要粗,黑鱼大多了。钓黑鱼不用蚯蚓而用小青蛙。把小青蛙捉来,用细绳拴住它的腿,细绳的另一头拴在渔竿上,渔钩钩住小青蛙的屁股。看到有黑鱼浮在水面,就把小青蛙一下一上地在黑鱼头上晃动,黑鱼以为是青蛙跳过,它就一冲而起咬住小青蛙不放,这时候莫迟疑,猛地起竿,一条大黑鱼就上来了。这家伙力大,得把它甩得离岸远一点,不然它会跳回水里去的。 黑鱼刺少,肉也嫩,很补人的。 严伍台的鱼啊,是黄家咀,雪友台的人们都羡慕死的。 羡慕当不得饭吃,只好把女儿们嫁过来。家里的人们吃不完了,让老婆带几条走娘家去。 另叫人羡慕的还多了,严伍台动物们也上得台面的。 老鹰是在天上飞的,它们定定地在天上,有时转几个圈儿,书面语叫盘旋,有时就歇在云端。当兔子或者鸡们在田里嬉闹时,它们就一冲而下,抓住猎物就走,让人的眼睛都来不及眨一下。它们算不得严伍台的动物。 大雁们一会儿一个人字,一会儿一个一字,晃几下就没了,自然也算不得严伍台的动物了。 刺猬当然是。 猪獾、狗獾、羊獾,其实就是野的猪,野的狗,野的羊。它们跑得快,我一次也没捉住过它们。倒是姚某喜的父亲会打铳,收工后,他就背只篓子,在林子里转几下,回家来时便收获不少了。他是我佩服的一个人物。 野的鸡飞得很快,不比抓鱼,我也奈何不了它们,也是姚某喜的父亲用铳打。铳是一根铁管嵌在一根树棍上,铁管的尾端有一孔小眼,管中放下炸药,还放下许多铁砂子,扣动扳机,火药点燃,砂子们就冲出去,往野鸡的身体里钻去。野鸡的肉不是很好吃,非得年轻的人,牙口好才能咬得动。所以小孩子们唱歌时就说:三岁的娃,会打铳,一打打只野鸡公,拿回去敬祖宗,祖宗咬不动,丢到茅厕里蹦几蹦。老人们不吃。我也不吃。我就去找姚某喜弄几根野鸡毛,像戏台上的武生那般,插在自己的草帽上,大声吓唬黄某青:常山赵子龙在此,快快下马受死。 严伍台家家户户都有竹林和树林。竹林多是靠近屋台,树林在竹林后面。小鸟多在竹林里,竹鸡子,白头翁、小黄鸟、麻姑嫩、夜壶鸟等都在竹林里。竹鸡子大一点,有点肉,别的就一个嘴巴,没什么好吃的。我打竹鸡子用弹弓,找根有叉的枝,一般是桑树的枝,再找一块自行车内胎皮,就成了弹弓。找一块小石子,麻雀蛋大小,包在胎皮里,用足劲拉开胎皮,石子弹出去,竹鸡子就落下来。有十来个,就可做一碗菜。它们的巢都在竹枝上,它们找来麻类的东西,用泥巴和口水糊成巢,一个小口只能容它们钻进去。即使下雨,那水也进不了巢的。巢都设在竹枝的尖端,老鼠和蛇都去不了的。夜壶鸟的巢和夜壶相似,不过它的巢很低,人们举手就可碰到它。当然,只有我和吴某天这样的小孩子们才去掏它的蛋,用火烤了吃。 麻雀不好吃,但好玩。下雪的时候,弄一个大的簸箕,用一根小树枝撑着,簸箕下放好多谷粒,雪天的麻雀饿坏了,就一古脑儿来抢吃食,只要把小树枝上的细绳一拉,麻雀们便都盖在簸箕下了。鲁迅精通此道。不过祖母不让这么弄,她怕菩萨骂她。只有哥哥弄过几回,我是看客,未曾动手的。 大点的鸟多在大树上。白鹄子最多了。严某林家后有根皂荚树,一到傍晚,去湖边的白鹄子们全回来了,都歇在皂荚树上,第二天一大早,它们又飞回湖边去了。皂荚树上有很多的刺,一根根大而坚硬,可以刺破人的肚皮。晚上没人敢去。 喜鹊是吉鸟,人们不吃。乌鸦是怨鸟,报丧的,人们怕吃。 严伍台的人们吃鸟不及吃鱼。 蛇、青蛙、癞蛤蟆,这里的人们不兴吃。 不过蛇,人们都恨它。它不但咬人,还吃鸡。一回,人们正在禾场打谷,一根青蛇爬上大柳树,要吃喜鹊蛋。刘某发果断决策,让姚某明一铳打了去,当即把蛇打死。青蛇无毒,但人们不吃它,只是埋了了事。 瓜果在严伍台并非特色。油瓜居多,生吃不好吃,不是很甜,只能用来腌吃。 南瓜冬瓜只能喂猪。不过,年,人们也吃得多。香瓜最好吃,但人们又舍不得用好田好肥种它,只有少数人家给孩子种一些,但没等长大,就被我、吴某天等偷了。 只有一种沙瓜,好吃又好种,家家都种得一些。成熟的日子,一到夜间,小家伙们三五成队,在夜色里忙碌,瓜皮到处都是。 果子就有桃李梨枣,到处都有,不算严伍台特色。桑枣子也是到处都有。枸桃子酸得无人吃,只有我吃,不值得一说。只有拐枣,怕是有许多人没见过的。我家屋台上就有一棵。成熟时,除了黄某青外,再好的朋友,如吴某天的,也休想上得树去。有胆大者,要知道弹弓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有次,罗某牛尝了一次,竟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那次,我被母亲大骂过。即使如此,我也不让人上树去,哪怕是好看的何某娥。我只让黄某青吃我家的拐枣子。 村里树多,杨树柳树桑树构树,桃树李树枣树梨树,鸡公树桂花树榔树泡桐树,竹也多,家家户户都有。竹有桂竹水竹之分。桂竹好做房子,水竹细些,只能能劈篾做篮子。 严伍台是个呈一字形排列的村子。她又并非笔直的一字。从村的西头走那么十来家,到了一个高台子,接着的村子就退后了约20米的样子,是竖折弯竖,后边这一竖就很长了。全村约有四五十户人家,人多,在这一带应该算个大的村子。外面的人对严伍台的呼叫不全是叫严伍台的。徐马湾一带的人叫她三湖园。顾名思义就是有三个湖围着。三个湖当然是青山大湖、青山小湖和长湖。长湖严格说来只是块湿地,白龙沟从湖中穿过。水少的时候湖中只不过小腿深,没有荷叶,人们也不去那里抓鱼。我一次也没去过,不知有鱼否。 严伍台的东边第一家是胡某四家。他家离谭李坡不过米。胡某四与我家还沾点亲,胡的妻子,我叫她姑婆,不过我们两家来往不多,这亲也就是远的了。严伍台的人们常说,这亲戚呀,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就完了。想想也是,倘若没完没了地往来下去,全村都是亲戚了,送人情都送穷的。有的人第二代就不来往了。如黄某堂的。他的儿子爱上了他妹妹的女儿,可妹妹的女儿不爱他儿子,结果那儿子就有点不太清楚了。平时不说什么,也不和人往来,但一旦来了精神,他就:“你们听好了,我是总书记,你们不听话,我就要批评你们……”因是这个样子,党支部的领导也不好说什么,你再大的官,总不能与一个不太明白的人去讲道理啊。 胡某四有个女儿,叫胡某娥,因耳朵不很聪,说话也不够好,不过为人很善良。她比我小一些,我还是很喜欢她的。因为没有弟弟,她母亲就给她抱了一个,叫胡某强的。可胡某强来后不多久,她又来了个弟弟。人们说,这个男孩子是胡某强引来的。生活中也确有不少这种事,夫妻没孩子,抱一个来后,就有了自己的孩子。严伍台的人说,有了自己的孩子,也要把抱来的孩子当作儿子看的。因为是他帮你带来的亲生子。还说若你嫌抱来的孩子,你的亲生儿子也会长不大。不知这有多少道理。不过严伍台的人都还好,有几户对抱来的儿子还好,胡某四对这个大儿子比对亲生的还好呢。 胡某四的弟弟叫胡某元,人们叫他马桶子,就是村里女人用的东西,很不雅的。胡某元个子长不高,很小时便没了父母,是哥哥养他到大的。人生得像武大郎,且说话没有武大郎灵光。30多了还没找个老婆,常受村里一干精亮人的幽默。我对此有许多不平。那些人也动不动就把我叫作**井的。 胡某元到了要老婆的时候,终于有了一个。那女儿只有一只眼,不过说话很灵光。第一次见面,胡某元搬了板凳,“您请坐!” 那女人个子与胡某元等高,丰满,落座后,头低着,偶而抬眉斜一眼胡某元:“您也坐。”说着还拍拍身边的板凳。 胡某元喜笑颜开地坐在了她的身边。 不想,这两人的称呼也被周某兵传开来:“您也坐。您哪!” 在严伍台,同辈人相称,你来你去的,不说您的。胡某元的您便成了村里人的笑谈。 我为此不平,看来严伍台的人未必明白举案齐眉的。 胡某元第二年便生子,一连三个儿子,个个都标准健康。严伍台的人就感慨:破窑也产好的瓦哩。 接过来是胡某年家,胡某四的堂弟。他有个哮喘病父亲,那老人成天气不足,活得好艰难。 李某喜居第三家。他家是贫农,屋台低,房也好小。他的几个儿子都很争气。其中一个,在水坑边抓青蛙,落下了水,还是我的父亲给救起的。那天也巧,我的父亲去水坑担水,正好碰到那个儿,当即就跳下水救起来。为此,李某喜的老婆还送了不少鸡蛋来谢。 李某喜的邻居是银叔,一个长有疝气的男人。因不能下地,且言语笨拙。 当然,没本事对于他而言,半点也不冤枉的。地里的活多是那个叫地儿的女子干的。所以严伍台的儿歌也为她唱了:“洗洗洗,洗白菜。洗到半夜不回来。鸡子叫,狗子咬,洗菜的地儿回来了。打开门,没得人,洗菜的地儿死得成。” 说起严伍台的儿歌,有外村传来,也有本村编的。 剐剐剐,剐蝌蚂,三片芦叶四匹马。上一坎,下一坎,来我家里吃早饭。 要五六个孩子一起玩的。 旁边走的什么人?走的张家老先生。来我的屋喝茶喝酒。不喝你的茶,不喝你的酒,单单捉你的梅花狗。 也是要一群孩子才能玩的。 不过他老婆倒还算贤慧,地里的活自己全包了。 银叔有两个孩子。大孩子是个女孩,长得有点姿色,多人来求,她都没看中过。后来找了一个渔薪的,是街上的,这才满意地嫁了去。 黄某青家就住银叔隔壁。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他们两家有过来往。只是隐约记得大人们说过,两家大人打过架,所以老死也不曾往来。 黄某青家是大房子,村里人叫它三屋头。屋子前面有两厢,两厢之间是个天井,采光,两厢后面是大厅,大厅两边是卧房。大厅后面还有几间房,叫拖檐。堆放杂物或者放大牲口,如牛马之类。算面积,相当于城里人的一栋别墅的。 黄某青的父亲很有些文墨,会诗会画。他写一些村里人弄不明白的东西。有一次,他写了个东西给我看,说是一个自创的词牌,叫什么伍台春。我由衷佩服他。能创词牌的人,大学教授也不见得有这水平。我小的时候,爱看些书,可父亲的那些个大学中庸,我一个字都不明白。黄某堂却对这个邻居的孩子好像还可引为知音,就借一些《火烧红莲寺》、《绿牡丹》给我看,这让我好生感激。他还会一点武艺,就画一些习武的路数图,给一些年轻人看。他画这些的时候,都是在西厢房里画的。那是他的书房。他画好这些后,从来都不会忘记给我一看。 不过他好像也并不欣赏我,他从来都不曾提过我与他的黄某青的事。 黄某堂过来就是杨某尧家了,这人是我的叔祖父,也是我祖父的亲弟弟。他们来到严伍台立嗣,分别顶替两户杨家的香火。叔祖父不像我祖父,虽是兄弟,性子大不一样。我的祖父很少言语,但叔祖父性子却很刚烈,也会些武。据说,曾被国民党旅的兵打过,他不吃药,只做了几场功夫,就身体好了。因此刚解放那些年,他还带了些徒弟,在家做功夫。他的功夫就是深呼吸气,慢放气,放气时就有许多的鼻涕,那些学生们总是顺手擦在鼓皮上——一种杉木做的壁。弄得那鼓皮像上了桐油一样,亮晃晃的。 叔祖父子嗣少。他也有过一个儿子,比我的父亲小不了多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天花,要了那孩子的命。叔祖母也因此而去。后来,他又讨得一个女子,生育力很强,但多是夭折了。因此,在我的哥哥出生之后,他曾强烈要求把这个侄孙子过继到自己名下,可我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她的一生都与这个孩子有不解之缘。叔祖父无奈,还把万家湖的田给了十多亩到自己的哥哥。那是好地,虽长一些芦苇,但比白龙沟的那些常常过水的地好上几百倍。就这样,我的母亲也没有答应。地给了,侄孙却没要上,这好像是个亏本的买卖。不过,坏事变好事。土改时,他竟因此没划成富农。本该是贫农的我的祖父,也被划成下中农。所以叔祖父后来也想得很通。兄弟俩也很是和谐。 不过命不太好的叔祖父晚年不好。他去漂草湖,也就是青山小湖割草,那年月老是没柴烧,他就到处割草。割草又不带水喝,就喝湖中的水,竟感染了盲肠炎。这本是个小病,但他舍不得花钱,一医院,一下花了多元。那时的多元,可盖一栋房了。要钱看病,他就卖了房的四分之一,而且再也没了那么好的劳力了。 叔祖父的房子和黄某堂的一样是三屋头,只不过他的房子没有拖檐。这次病后不几年,他就去世了。死前,因无儿子,他就对我的父亲,也是自己的亲侄儿交待:他死后,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把这屋子的中柱换掉。我的父亲点了头。我不明白,好好的房子换中柱干什么。我的祖母说,这屋子是叔祖父从阴阳台的一个绝户人家搬来的。绝户人家也就没有了子孙的人家,是个不好的房子。而且房子的中柱是倒的,算命的说,这屋子虽大,只能容两个人,多了两个,多余的人就要出毛病。还有出奇的是,有个叫金海的一家人在他家住过几年,就常见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吓得小孩们哇哇叫。叔祖父年轻时阳气旺,倒还好,他一老迈毛病自然就多了。 叔祖父死时,好的棺木都没有,用几块柳树板一拼后,就葬在了一块棉花地里,坟堆也没起一个。想来人是怪可怜的。好在他的后人都好,女儿招了个女婿,有女儿也有儿子,而且孩子们个个健康。计划生育时代,虽罚了几千元,但这足可告慰叔祖父的在天之灵了。 叔祖父与黄某堂家之间有个很宽的巷子。平日人们去村后种地与收割,牛与犁都是从中而过的。到了夏天晚上,这里是乘凉的好去处。那风总一阵阵消去人们许多炎暑。 夏日晚上,我总是把自家门板卸下来,再搬两条长板凳,门便放在长凳上。自己便睡在门板上,有时弟弟也睡上面。不过他从来不搬门板。严伍台园子大夜蚊子也多,这时,祖母就坐在孙子的一旁,为我们用扇子驱蚊。祖母是小脚,用裹脚布裹脚的。那脚总是不好闻的。祖母有时就故意逗孙子,让我们闻她的臭脚,而后哈哈大笑。祖母还常常让我吃她的奶,一点奶水都没有,我自然不愿吃的。祖母就把孙子的头贴在自己的奶上,而后又哈哈大笑。我长大后才知道那是一种叫作天伦之乐的。我好想报答祖母,可是祖母去得太早了。我只是在后来和弟弟给祖父母立了个碑。 天门文艺投稿邮箱: 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gtoujiana.com/dtjyl/5316.html
- 上一篇文章: 怎样给兔看病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